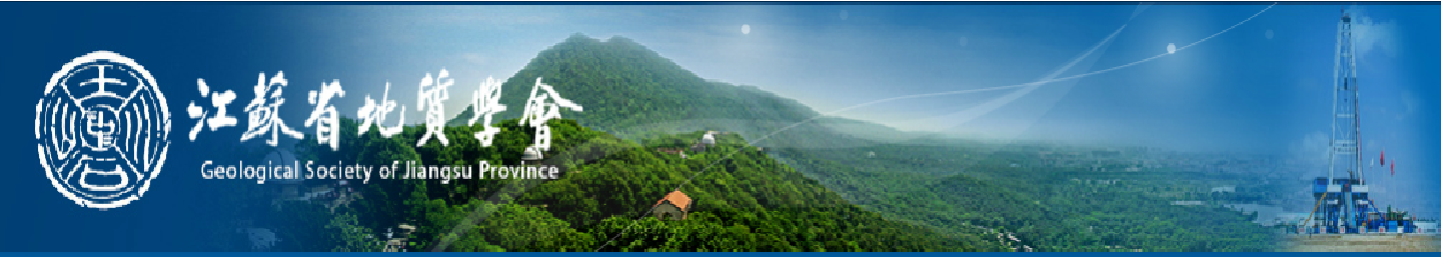
摘要:全面回顾了8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丁文江研究状况。战争及动荡的时局,是阻滞丁文江研究的主要因素。丁文江逝世后的前二十年,对丁只有纪念而无专门研究。1950-1970年代,从事丁文江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学者。进入1980年代后,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下一步的丁文江研究,将通过新思路、新方法转入摸高探深的新阶段。
关键词:丁文江 研究 述评 丁文江(1887-1936)属于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不凡实绩而长期不被重视的人物。丁文江研究之兴衰沉浮,与时代密切相联。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动荡的时局,是阻滞对丁研究和客观评价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大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丁文江研究。对过去八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丁文江研究做一番梳理与评述,是深入研究丁文江的基础性工作。 一、 纪念推动研究 1936年1月丁文江辞世后,与他有关系的几个刊物都出有纪念号。《独立评论》的“丁文江纪念专号”最早,在2月印行,共发表傅斯年、胡适、翁文灏、葛里普、黄汲清、杨钟健、吴定良、周诒春、蔡元培、陶孟和、李济、汪敬熙、凌鸿勋、朱经农、丁文涛、丁文治、高振西、张其昀等纪念文章18篇。这些文章可分五类:通论丁之生平,专论丁之科学贡献,丁与中研院,丁之传记材料,著作目录。[①]后来,该刊又发表傅斯年、杨济时、钟伯谦、刘基磐、胡振兴、李毅士、汤中、竹垚生等人的纪念文章。《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丁文江先生纪念号” 于同年6月印行,除刊有翁文灏、卢祖荫、章鸿钊、李学清、黄汲清等人的纪念诗文外,余皆为地质学研究论文,内容“多是丁先生生平兴味所在,或研究未竟的各种地质问题”。[②]作者有:章鸿钊、田奇瓗、尹赞勋、马廷英、叶良辅、李捷、杨钟健、谭锡畴、孟宪民、王竹泉、谢家荣。《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6卷系“丁文江先生纪念册”,于次年印行,刊有章鸿钊挽词、翁文灏所作《丁在君传略》以及李四光等人的论文20篇。此外,为表彰丁对中国科学的贡献,1936年,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央研究院分别设立“丁文江纪念奖金”[③]、“国立中央研究院杨铨、丁文江奖金”[④]。1937年1月5日,中研院史语究所在南京,中国地质学会北平分会、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三单位联合)在北平,分别举行了丁文江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中央地质调查所联合举办了丁文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1947年,中研院决定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更名为在君纪念馆。1956年,台北中研院为纪念丁文江逝世二十周年,特出版《丁故总干事文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该院院刊第3辑),内容分三部分:传记(共胡适、朱家骅、阮维周、董显光、蒋廷黻、董作宾、罗家伦、李济等人所作传记、回忆文字8篇)、纪念论文11篇、遗著选辑(包括《漫游散记》、《苏俄旅行记》等6种)。纪念活动不仅能重新激活丁文江在世人中的印象,而且由它催生的纪念文章、专书,有的已对丁在科学上、政治上的建树有了精要之评价,有的则为进一步研究丁之事业、生平提供材料和线索,是丁逝世后60年里丁文江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在1949后的三十年间,丁文江在大陆是被打入“另册”的。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潮流,他才逐渐被重新发现和评价。在1980年后的中国,写怀念丁的文章,组织对丁的纪念活动,不仅具有为丁平反的特殊义涵,更直接推动了对丁之研究。1985年,湖南省政府重新修缮了位于岳麓山的丁文江墓。次年,由湖南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和宣传部长出席的“丁文江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在长沙举行,与会者高度赞扬丁对中国地质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等于是为丁平反。1987年丁文江诞辰百年之际,北京大学与中国地质学会联合举办了“纪念丁文江100周年、章鸿钊110周年诞辰——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研讨会”。这是大陆上首次举办丁文江研讨会,有不少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⑤]两次高规格纪念、研讨活动,重新确立了丁作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地位。2007年,湖南地质学会又重新修缮了丁文江墓。是年及2017年,泰兴市党政当局先后举办纪念丁文江诞辰120周年、130周年大会。要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影响丁文江研究的种种窒碍,都不存在了。在台湾,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和中研院也于1987举办了丁文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包括学术演讲会、丁文江奖章颁赠及出版纪念专刊三种方式。 二、丁文江遗著之整理、出版 (一)、《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丁文江逝世后,留下大量未定稿的地质报告(包括他人根据丁发现的材料而撰成的论文和报告)、地质图幅、地质剖面以及地质考察时的标本登记、气象和经纬度测定记录,各种照片,人类学文稿,旅行笔记、日记等。至于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也没有系统搜集、整理。为纪念丁文江,1936年1月26日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2次年会决定委托尹赞勋、黄汲清整理丁氏文献中最大宗的地质、地理类部分。而有关人类学方面的稿件由民族学家吴定良整理,与地质无关的旅行笔记和游记,则交由丁文渊保管[⑥]。整理丁氏遗著,绝非易事,一则丁氏遗稿数量庞大而又散乱,虽经尹、黄二人先后予以清点,还是很难理出“一个分类系统”。更重要的是,次年日寇即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尹赞勋先在江西服务,后返中央地质调查所任副所长;黄汲清亦先公务繁忙,继又赴甘肃新疆调查,所以两人都无暇顾及丁先生遗稿之整理。”故,在尹赞勋将丁遗著中相对完整的《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整理出来并发表后,[⑦]整理工作被迫停顿。1944年春,李四光、丁文渊均过问丁文江遗著整理工作,希望此一工作早日完成。丁文渊与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及周赞衡一起洽谈,讨论了编辑方法、出版方式等问题。这样,整理工作于同年5月正式开始。次年,由黄汲清、秦鼐等担任贵州、四川、广西部分业已完稿,图件亦将次绘竣,尹赞勋、边兆祥担任云南、西康部分亦完成大部。次年春,整理工作告竣,惟因物价飞涨,无法立即付印。10月,李春昱、丁文渊、黄汲清商定:将编辑好的《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带到北平印刷,印费则由李、丁二人向各有关机关募捐。又因物价持续上涨,决定一面募捐一面付印。12月,文稿交北平中西印字馆排印。1947年夏,《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终于出版。[⑧](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而且在近代年谱编纂学上具有典范意义。梁氏逝世后传记作品不下几十种,但能超越此谱者,尚不多见。与梁启超私谊颇笃的丁文江对编纂梁谱甚费苦心,但直至其逝世,此书也未最后定稿。丁氏挚友翁文灏约见协助丁文江编撰年谱的赵丰田,请其继续工作。1936年3月,完成第一稿,又经张其昀详为校阅,5月完成第二稿。在翁文灏主持下,将此书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家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⑨]但很快,抗战爆发,所有修订、出版事宜被迫停顿。丁文渊一直希望这部年谱能早日面世。但翁文灏认为,在战乱时期,只有将书稿交给一个公家的学术机关保存方能对得起老友丁文江,并委托历史语言研究所保管。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认为当时无法出版,除了战乱,梁启超长女梁思顺也因谱中引用家书太多不愿早发表。抗战胜利后,梁思顺改变主意,倒希望该书早日出版。但内战正酣,物价飞涨,出版之事根本不可能。后来,傅斯年将史语所迁到台湾,书稿也被一同带走。但战后台湾,经济困顿,史语所带走的珍贵藏书和手稿都被堆压在书箱里不得上架。直至1955年,这部久经磨难的原稿才重见天日,在丁文渊的推动下,此书被冠名以“梁任公先生年谱稿”于1958年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⑩]此谱是在1936年油印本发出后未再进行进一步修订的情况下出版的,故名之以“稿”,倒也实事求是。台北版梁谱出版后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此书的出版事宜纳入议程。1978年夏,仍健在的赵丰田先生应出版社之约,对1936年的油印本加以修订,修订原则是:在基本保持原《初稿》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作适当的增补和删改。增补侧重于信札和有关谱主活动的重大史事,特别是解放后发现的一些与梁氏交往的信札,如《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删改仅限于与谱主关系不大的极少量一般资料和原有的编述性文字。此外,还对原《初稿》作些资料性的校勘和注释。[11]最后的修订本《梁启超年谱长编》于1983年出版。从以上两种文献的整理过程,可见战乱及左的年代此事推行之艰难。至于其已刊文献的结集出版,就更谈不到了。[12](三)《丁文江选集》、《丁文江文集》、《丁文江卷》黄汲清是丁文江的学生,受丁影响大而对丁崇仰有加,在1980年代纪念、重评丁文江的各项活动中,黄作为当时地质界的权威人物多积极推动、参与,出力甚大。同时,黄氏大力倡导研究丁文江,他曾最早倡议成立“丁文江研究会”,以专门从事丁文江研究。1980年代中后期,黄与潘云唐、谢广连合编了《丁文江选集》,共收丁氏地质学方面的论文20篇。书前有黄之长序,全面评述了丁在地层学、区域地质、地质图及区域地质测量方法、矿床学、矿业及矿物、中国的造山运动、古生物学、工程地质学、地理学、川广铁道线路初勘报告等方面的卓越贡献,是难得的一篇研究丁氏地质学贡献的论文。该书早在1990年即已编好,但因出版经费问题迟至1993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欧阳哲生编《丁文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共七卷:科学评论、序跋、时评政论、英文作品;《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 》;丁文江地质调查报告续编;《动物学》、《民国军事近纪》、《徐霞客先生年谱》;《爨文丛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游记、书信、诗歌、附编。宋广波编《丁文江卷》,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一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内容包括:丁科学方面的文章、政论以及游记。科学方面的文章,主要侧重于普通读者易懂的部分,专门的地质学论文(多数用英语撰写)尽量不收。政论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基本都收入了。游记系《漫游散记》、《苏俄旅行记》两种。 三、 起步晚而方兴未艾之“丁文江研究” 丁文江逝世后的前二十年,对丁只有纪念而无专门研究。自1956年台北举行丁之纪念活动之后,丁文江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其后近二十多年里,从事丁文江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学者。进入1980年代后,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一)1950-1970年代之丁文江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胡适编《丁文江的传记》和夏绿蒂·弗思(Charlotte Furth )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胡适编《丁文江的传记》丁文江逝世后,其挚友傅斯年希望胡适为丁作传,如胡不作,他将自告奋勇来写。在傅看来,胡适是最有资格为丁文江写传的人。但其后因战乱不断,且傅氏本人亦早逝,所以丁之传记迟迟不得问世。1956年,台北中研院的纪念活动终于催生了这部迟来的《丁文江的传记》。作为第一部相对完整的丁传(全书只有12万字),其首要的意义当然是“补白”。其次,该传提高了丁文江的地位。[13]第三,它是胡适根据其新传记理论所作的新式传记的示范作品。[14]第四,此书面世六十多年后仍无一部更好的《丁传》来取代它,仍具重要参考价值。但今日看来,其不足十分明显:此传的参考材料主要来自《独立评论》上的纪念文字,似乎是根据这些文字“编”成的,胡适本人自署“编”,而不是“著”。但此书近年来在大陆上不断翻印时,均署“胡适著”,这是不确的。至于丁之信札、日记、笔记及大量已刊、未刊著作并未参考。此外,胡适说,“我不是学地质学的人,所以我不配评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专门学术,这是更大的缺陷。”[15]如果不评述丁对中国地质学的功绩,怎么可以呢?李敖也曾指出此传之其他不足:史料引用时有时失之细校,如没有弄清赵亚曾殉职时的年纪,有些地方失之太略等。[16]所以,太需要有一部更完备之《丁文江传》来取代此书了。此一时段台湾的散篇丁文江研究文章,绝大多数收入朱传誉主编《丁文江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2、夏绿蒂·弗思(Charlotte Furth )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本书主要研究的,是丁文江一生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科学活动与科学思想,政治思想及政治实践。关于前者,作者说:丁“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以科学思想教育同胞为己任。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丁强调的是科学方法。丁文江对进化论的认识,也与严复宣扬的进化论不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丁文江的科学活动与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起来,认为丁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与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提法是不同的。长期以来,在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在此前后中国科学人的科学研究、科学传播活动是不在关注范围之内的。而五十年前,一个西方学者最早做这样的阐释,是格外难得的。关于丁之政治活动,通过对办《努力》周报、任职淞沪总办的分析,所得结论也新颖而恰如其分。该书还将丁定义为“东西方之间的理性主义者”,鞭辟入里。虽然,本书时代局限性(不少的史实描述错误,缺乏对历史大背景精准把握等),但仍然是不能绕过的丁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二)1980年代后之“丁文江研究” 1、丁文江的科学活动与科学思想1980年代的丁文江研究主要集中于丁之科学贡献与科学思想,尤其是丁在地质学方面的成就。黄汲清、夏湘蓉都有高水平论文。[17]王仰之编《丁文江年谱》虽简略且不乏史实性错误,但这是一部代表当时研究水平的书,其侧重点依然是丁之地质学方面的建树。以上论著的主要结论: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之后,虽然研究丁与中国地质方面的论文日少,但也有论者根据新材料研究指出:丁是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最重要的奠基人。[18]关于丁文江在其他学科方面的贡献。有学者评述了丁对徐霞客研究及编撰徐氏《年谱》的贡献,认为丁对徐学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评价准确、中肯,确立了该书在中国科技史、世界科技史上的应有地位。[19]有学者指出,丁文江整理的《爨文丛刻》“是中外出版的彝文经典著作中唯一的一部巨著”。[20]丁以上著作的奠基性意义还表现在:它们在1980年代都得以修订再版,依然是所在领域的首要参考著作。此外,丁对地理学、考古学的贡献,亦受到学界关注。[21]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关键性事件之一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历来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不独专门的近代思想史著作有专章论述,对此论战的专题研究亦汗牛充栋。综观这些研究,其研究角度之多元,研究层面之深广,都是少见的。比如,有的是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有的是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的角度,有的则将其视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开端,等等。任何角度的研究都是需要的,也只有更多视角的研究才能更有助于深刻理解和认识这场论战。这些研究,当然无法绕过兼论战挑起人和主将双重身份于一身的丁文江。改革开放后,对这场论战的研究,也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程,学术界逐步抛弃了将这场论战是“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的定性,而认为科学派也有唯物论者。而其后三十多年间,随着对论战的研究更加深入,就越能凸显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就越能凸显作为论战挑起人的丁文江的重要性。在对这一研究领域,有一种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把丁文江视为中国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22]事实上,科学主义是科学高度发达时候的产物,在1920年代初,中国科学还是刚刚起步,大多数国人尚不知科学为何物?且丁文江本人也并没有将科学视作一种信仰。所以,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2、丁文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自1980年代末,丁之政治思想、政治活动开始进入大陆学者视野。其第一篇论文是研究丁晚年的政治思想,认为丁政治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主抗日,反“剿共”,同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23]这说明,学界已跳出贴标签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客观、实事求是。有论文将丁之政治思想概况为四方面:好人政治的拥护者,暴力革命的反对者,抵抗日本侵略的低调,主张新式独裁。[24]其后,学界研究丁政治思想和实践的热点问题有三:“好政府主义”、任职淞沪总办、民主与独裁论战。有论文认为,无论丁之“好政府主义”,还是新式独裁,都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精英政治。[25]不少论文研究了丁任职淞沪总办这一重要事件,不再简单地将丁认定为“反动军阀的帮凶”,而多指出其正面意义:规划大上海的新市政,部分收回会审公廨的利权。有论文认为丁之政治倾向形成于其留英期间,其政治思想与实践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理念,均围绕国家、民族的利益展开,而这种政治理念无法适应近代中国情势,导致其政治抱负无法实现。[26]当然,也有论文指出丁政治思想的局限:关心政治,而不懂真正的政治;同情民众,但看不到民众的革命力量。[27]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不能不提到唯一的一部专著——谷小水著《少数人的责任》。该书颇为全面、深刻地的研究了丁之政治思想,对丁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任职淞沪总办及“民主与独裁论战”等均有颇为独到之见解,认为:在丁之政治思想中,“‘少数人’的责任统贯全局”,其知识分子性格使其扮演的角色也是“少数人”,他是“五四”时期及以后中国思想界的重心之一。显然,大陆地区的丁文江研究,经历了由低而高、由浅而深、有窄到广这样一个继长增高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制约丁文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最大因素是史料之不足。在最近的十年,有关丁之不少新材料被挖掘出来,而材料的扩充必将成为推动丁文江研究的新动力。何汉威介绍了台北史语所收藏的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时大量往来函电。[28]2008年9月出版的拙编《丁文江年谱》也挖掘出大量前人不曾注意的新材料,如:丁文江从未发表的地质报告的手稿,丁在北洋政府任职的各种任命书,丁文涛撰《显考吉庵府君显妣单太恭人行状并序》等等。以新材料为基础,纠正了此前一些错误或模糊不清的说法,如:丁文江1904年抵达英国的确切时间,丁首次赴北京任职的时间是1913年1月,先任佥事,后任科长,而以往都认为是1913年2月到北京任职,且直接任地质科科长;丁文江是首任地质研究所所长,而以往认为章鸿钊是该所的首任所长等等。此外,李学通根据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收藏档案,研究了丁文江留英学费问题。[29]2011年笔者发现迄今为止最能反映丁学业完成前思想的《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30]台北学者刘素芬根据全国经济委员会和中研院档案,研究了丁文江筹办棉纺织染实验馆的过程和影响,认为这是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统制经济的实践。[31]韩琦发表并简介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等三家单位收藏的丁文江与友人的27通往来英文信。[32]张雷编《丁文江海外书信集初编》(学苑出版社,2017年11月)收入发掘自美、英、澳等地档案馆、图书馆的丁文江与外国友人通信近100通。等等。(三)未来丁文江研究之展望经几十年之积累,丁文江研究已经走完了起步阶段,下一步理应进入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首先,对已经得到关注的老问题,诸如“丁文江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任职淞沪总办”、“民主与独裁论战”等需要将其放在更为长远、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运用新思路、新视角从事更进一步的“摸高探深”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跨学科的研究”,不仅仅因为这种研究更有助于探求历史本真,更因为丁是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次,丁文江研究资料的扩充工作在近十年虽有大进步,但仍有进一步拓展之广阔空间。资料主要包括丁氏著述、函电及相关之生平、传记材料等,它们现仍沉睡于公私档案(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档案,上海档案馆和台北史语所藏丁任淞沪总办时档案,与丁文江有关系的海外科学机关的档案馆图书馆等)、报刊杂志中。新材料之被发现,一方面可生发出一些新问题,有利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在时机成熟时可编纂一套权威的《丁文江全集》。所谓“权威”,首先要“全”;其次要慎选版本,有手稿的必须尽量以手稿为底本,至于书信,应考实其书写年份;编纂体例、分类要科学。
[①] 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总第188号,1936年2月16日。
[②] 谢家荣:《编后》,载《地质论评》第1卷第3期,1936年6月。[③] 自1940-1948年,先后获得此奖的有:田奇瓗、李四光、黄汲清、尹赞勋、杨钟健。[④] 自1938年起,先后获得此奖的有:吴大猷;许云樵、田汝康;陈省身等。[⑤] 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地质论评》,1936年第1卷第1期,81-82页;黄汲清:《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编辑后记》。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丁文渊保管的这部分文献是下落不明的,学界常引此为憾事(可参谷小水:《少数人的责任》,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9-10页)。这部分材料究竟归落何处?2008年,笔者访学于台北中研院,在近代史所档案馆发现了丁文江滇游人种见闻、旅滇日记、留英学费档案等材料,与此处所说丁文渊保存者极为吻合。这批材料,是香港张万里先生捐赠的(证据是吴大猷院长复张万里函,附后)。而丁文渊在1949年以后直到病逝是居住在香港的,因此笔者甚怀疑张万里捐赠的文献来自丁文渊,于是遍询丁氏后人:在丁家戚友中,“有无一位张万里先生”?但得到的回复都是否定的。因此,张捐赠的这批材料与丁文渊的关系,尚须进一步追查。附录吴大猷复张万里函:万里先生道鉴:周元燊先生来台,转来尊赠有关本院故总干事丁在君先生资料,其中包括滇游人种见闻、旅滇日记手稿以及当年办学文件等,均已妥收。除交由本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于该所“院史室”以供研究参阅外,特函奉达,谨对先生惠赠之盛意,敬致谢忱。祉颂道祺 吴大猷敬启 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档号073-03-001)[⑦] 《地质专报》,乙种第10号,1937年。[⑧] 《地质论评》第3-4期,193页;黄汲清:《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编辑后记》。[⑨]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黄山书社,1994年,306页;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⑩]丁文渊:《梁任公先生年谱稿·前言》。[11]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12]丁文江的七弟丁文治在乃兄逝世后有做此事的的愿望,他曾有搜集《努力》、《独立评论》上丁文江文章的打算,并拟“出一分类的文存或遗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3册,270页)或许也因时局关系,此事不了了之。[13] 张朋园为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所写的书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3年第1期。[14] 李敖:《评介〈丁文江的传记〉》,《文星》第63期,1963年1月1日。[15] 胡适:《校勘后记》,载《丁文江的传记》,台北胡适纪念馆印行,1973年,122页。[16] 李敖:《评介〈丁文江的传记〉》。[17] 黄汲清:《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夏湘蓉:《缅怀忠于发张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丁文江先生》(以上二文均收入《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黄汲清:《〈丁文江文集〉序》。[18] 参见拙稿:《丁文江与中国地质事业初创》,《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19] 陈江:《丁文江与徐霞客》,载《地理研究》第5卷第1期,1986年3月。后续研究则有朱亚宗(其文《徐霞客是长江正源的发现者》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20] 马学良:《增订〈爨文丛刻〉序》(《增订〈爨文丛刻〉》,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又参:任继愈,《彝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爨文丛刻〉(增订版)》,《文献》,1990第2期。[21] 李根良:《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地理学的贡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沈颂金:《丁文江与中国早期考古学》,《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22] 可参考郭颖颐、林毓生、高力克的研究。[23] 高泳源:《丁文江晚年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24] 沈庆林:《丁文江的政治思想》,《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25] 李卫平、周含华:《丁文江政治思想探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26] 孔祥宇:《丁文江政治思想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27] 刘启峰、肖宁:《丁文江任职淞沪总办浅议》,《史林》,1996年第1期。[28] 何汉威:《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的收藏原委、编辑整理及史料价值举隅》,《古今论衡》第12期(2005年)。[29] 李学通:《丁文江留英学费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30] 研究报告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年第2期。[31] 刘素芬:《抗战之前统制经济的实践——以丁文江的棉纺织染实验馆为例》,《东北史地》,2016年第2期。[32] 韩琦:《美国所藏丁文江往来书信(1919-1934)》,《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