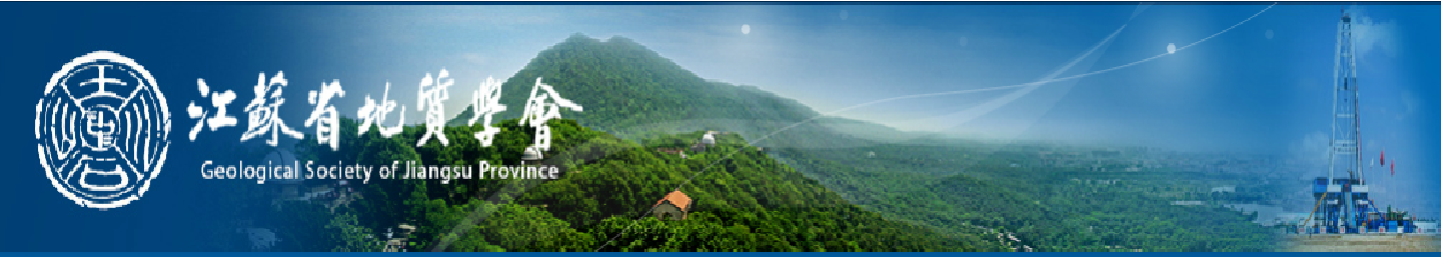
科学家的经济收入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如同女士的年龄一样, 个人经济收入属于不该涉及的话题, 这是现代社交礼仪中的N 项基本原则之一, 看那架式, 大概也还要坚持N 百年不动摇。不过, 像个他人隐私的爱好者, 历史学家们常将古人的如厕方式、沐浴地点, 乃至房中之术, 都一一放大, 陈列于世人面前, 至于个人经济收入, 自然也难逃法眼, 不在话下。当然, 他们讨论科学家们的经济收入, 并非真的是出于对他人隐私的爱好, 实在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乃至多重的现实意义。
虽然近代科学自欧西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不短, 但科学研究在中国成为一种职业还不到一个世纪, 到今年恰好90 周年。90 年前的1916 年, 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 该所成立的“法定日期”虽为1913 年,但科学家们谦称1916 年以后的工作才真正具有科学价值, 故一向以该年为成立纪念日。) 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历史亦由此开端。
在体制化以后的科学事业中, 从业者所能获得的经济报酬, 不仅是维持科学家及家属物质生活的经济来源, 同
年, 科学体制化在中国初露端倪, 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学家尚未形成规模, 社会角色分配中, 官本位色彩浓重的中国很自然将他们划入官的队伍。而职务的专业性特征, 又使他们成为官员行列中特殊的一队———技术官。从最初成立之时, 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就被列入政府官员序列, 其薪金标准自然也是与官为伍。
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为例。从1916 年至1938 年, 翁文灏始终在地质调查所工作, 其职务由最初的地质调查所矿产股股长, 渐升至地质调查所会办( 副所长) 、代所长、所长。其间还兼任过矿政司的科长、农商部的技监等职。其薪金收入的变化, 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科学家的经济收入颇有帮助。
据其后来回忆: 自欧洲获地质学博士回国之初, 有人约他“到地质研究所( 1913 年成立的地质专科学校, 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如谢家荣院士、王竹泉院士等) 去教书, 薪水是60 元一月。”1915 年初, 他正式获聘为地质研究所“专任教员”, 月薪定为200 元。1917 年2 月, 已任地质调查所矿产股股长的翁文灏又被任命为农商部佥事, 叙五等官,“给第六级俸”。按北京政府的官等法、官俸法等法律规定, 其月薪应为220 元。不久“改给第五级俸”, 升为240 元。1920 年初, 翁文灏升为四等文官, 给第四级俸, 月薪280 元。次年2 月, 再晋至“第三级薪俸”, 月薪300 元。1923 年3 月, 农商部任命翁文灏为该部最高技术职衔———技监( 相当于今天某某部总工程师) , 准叙二等官,“给技监第六级俸”。六级技监的月薪为550 大洋。
不知道从实际购买力上相比那时候的大洋与今天货币是如何的兑换, 想必总有三五十倍的样子。如果说由于翁文灏担任行政职务, 其薪俸水平更多反映官员的特点, 与一般科学家相比或许并不完全一致,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纯技术官员的薪金水平。
按照北京政府1912 年11 月颁布的《技术官官俸法》, 政府系统的专业技术官员分为简任技监、荐任技正和委任技士三等。其月薪具体为: 技监分1- 6 级, 800-550 元; 技正为1- 12 级, 440- 220 元; 技士分1- 14 级, 165- 25 元。当时地质调查所一般科技人员, 大学毕业初入所时的薪金约为三四十元。例如, 北大地质系1924 年毕业的乐森寻, 经地质调查所考试合格录取为练习生, 月薪标准是35 元。这应该属于尚未正式列入技术官等的实习期“津贴”, 不是正式薪金。但是“海归”们的薪俸明显高于国内大学毕业者。1919 年刚刚由德国留学归来以“派在地质调查所办事”的王烈, 即被授予“技正上任事”,“月给薪水银120元”。按说这也是临时过渡性的薪金, 因为按照官俸法, 技正中最低月薪起码也应该是220 元。
章鸿钊的薪金也许更具有代表性。章鸿钊1911 年自日本东京帝大留学归国, 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地质科长, 后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主持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 1916 年后任地质调查所股长、技正等。1922 年9 月, 这位从事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已10 年的中国地质学奠基人, 被晋升为技正第七级, 月薪是320 大洋。应该说, 他的收入与当时在大学任教的知名教授们相比也算是高的了。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月薪为300 元, 教授周作人的月薪是240 元, 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120 元。( 在图书馆打工的毛泽东, 每月工资8 个大洋。) 当然, 与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外国顾问、技师们的薪金相比还是难望项背。1914 年农商部聘来瑞典地质调查所前所长安特生( J. G. Andersson) 为矿政顾问, 其年薪达到18000元。他的助手、法籍技师新常富( Nystrom) 的年薪也有8400 元。
对于章鸿钊们的高薪, 其实也不必羡慕, 因为法律上的薪金不仅不等于实际的收入, 更不等于真实的生活水平。每个人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方式的不同, 家庭经济负担轻重的不同, 同样的薪金, 经济生活水平也大不一样, 更何况法定的薪金也常常不能保证。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府财政日现窘相, 官员的薪俸不仅常常不能按时领到, 甚至折扣发给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从同时期在北京政府中任职的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到, 从1916 年开始, 薪俸拖欠的事越来越经常。1921 年以后一次性领取全薪已经成为希罕事。被鲁迅先生称为“零割碎肉”式的薪俸, 往往还要再减去各式各样摊派性的捐献。这种没有保障的经济收入, 不能不影响到科学家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乃至科学工作。原本相约集中力量推动中国地质事业绝不兼差的地质调查所同人, 因欠薪多了, 也不得不到大学里兼课。翁文灏先在师范大学兼少数的钟点, 以后到清华兼做
地学系的教授及系主任。首任所长丁文江因为要负担着家中众多兄弟的生活与学业, 只得辞职“下海”, 去做北票煤矿的总经理。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入所工作的青年学者赵亚曾, 因“家本寒素”,“月薪微薄, 又不能按时发给”,“竟有弃学改业之意”。为留住这难得的人才, 所长翁文灏将商务印书馆请其校阅书稿的工作, 转请赵亚曾等青年学者“代任分阅, 移赠校费, 始克暂为维持”。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权, 地质调查所在改隶南京政府农矿部初期,经费更是异常窘迫。据丁文江所记, 翁文灏因“生活很难维持, 又因为要作太多, 常常生病”。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文官、技术官任用及俸给的相关法规条例, 政府官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和委任四等。其中正部级为特任官, 次长以下分简、荐、委三等。简任官( 大致相当现在副部至司局级) 又分为8 级, 荐任官( 相当于处级) 分12 级, 委任官( 相当于科级) 分16 级。
作为政府体制中技术官员的科学家, 其技术职衔分为技监( 简任1- 4 级) 、技正( 简任3- 8 级, 荐任1- 9 级) 、技士( 荐任1- 10 级, 委任1- 12 级) 和技佐( 委任2- 13 级) 四等, 薪俸自然是与其级别相联系的。按照南京政府1933 年9 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 技术官月薪如下: 简任技监680- 560 元; 简任技正为600- 430 元, 荐任技正为400- 260 元; 荐任技士为400- 220 元, 委任技士为200- 75 元; 委任技佐为180- 70 元。
具体到地质调查所科学家薪俸收入的情况, 我们找到一份该所土壤研究室科学家们1937 年的薪金表。当时中国现代土壤学刚刚起步, 相对而言成果尚不显著,科学家也还在成长之中, 薪多水平也不是很高。当时大学毕业入所尚未满2 年的练习员, 月薪为60 元。1935 年北京大学毕业入所的刘海蓬, 工作刚满二年, 月薪尚处于技佐中最低的70 元。1934 年大学毕业的宋达泉月薪为100 元。月薪最高者为该研究室主任侯光炯, 月薪120 元。侯光炯系1928 年大学毕业的。
另一份北平分所( 地质调查所1935 年迁南京, 北平设一分所) 1936 年7 月的薪俸表显示, 该分所专业技术人员中月薪最高者为220 元, 最低者为65 元。与之相对比, 该所行政事务人员和辅助性工作人员工资最高者为120 元, 最低者为22 元。而四名临时雇用的工役人员, 工资分别为: 15 元、12 元、10 元和9 元。总体而言, 在抗战前数年, 地质调查所事业经费已经比较充裕, 科学家们的薪金也较有保障, 但收入依然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些困难, 地质调查所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是其他机构或地方政府合作, 以合作方调任或外聘工作名义, 由合作方以津贴名义支付参与工作的科学家薪金。合作方支付的津贴一般超过所内薪金, 至少不低于所中水平。这样一方面增加了科学家的收入, 同时所内薪金暂停支付( 不领双薪) , 也节省了本所的经费。
二是从社会渠道为收入过低者筹措津贴补助。1937 年初所长翁文灏即以所中职员“薪给素薄, 无法调整”, 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 将该基金会给予地质调查所的“补助款项内全年酌提3000 元, 藉为薪给过低者每月津贴之用”。中基会函复同意。
抗战爆发以后, 地质调查所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起初后方经济形势尚好, 物价还未大涨, 科学家们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有保障的。随时战争的持续, 后方人口的增多, 生产能力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 西南与西北后方经济越来越困难。特别是抗战中期以后, 混乱的战争环境下, 经济动荡、物质馈乏、通货膨胀。1944 年时, 重庆的猪肉达到每斤90 元。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生活日感压迫, 难以维持生计”。所长李春昱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 自己感觉“无时不在困难中挣扎”。
战时科学家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呈现以下特征:
1, 法定的薪金与战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例如, 1940 年调入地质调查所工作的王超翔( 1937 中央大学毕业) , 入所之时起薪标准为75 元。1941 年10 月被任命简任技正的黄汲清, 薪金为简任七级, 月薪460 元。这还都是1933 年的薪俸标准。
这是一份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1945 年的月薪表:
———————————————————————
职衔 月薪( 元) 职衔 月薪( 元)
所长 520 会计主任 240
简任技正 460 会计佐理 160
荐任技正 340 人事管理 160
荐任技士 320 人事管理 140
委任技士 200 事务员 200
委任技士 180 事务员 140
技佐 180 雇员 70
技佐 160 测工 45
荐任事务主任 300 公役 45
————————————————————————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 地质调查所职员抗战时期与战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而政府下拨经费拖欠, 再度成为经常现象。譬如, 地质调查所1942 年下半年的特别办公费( 19200 元) 和1943 年1- 3 月的职员生活补助费, 直到1943 年3 月还未拨到。所长李春昱只得以“本所职员生活窘迫”为由, 向经济部提出暂借10 万元的申请。从档案中我们看到, 直到1943 年8 月, 李春昱尚在呈文催请拨发地质调查所1942 年下半年度及1943 年度的特别办公费( 38400 元) , 以及1943 年度7- 12 月生活补助费。
2, 生活补助与米代金超过标准薪金, 增进职员福利措施效果甚微。对应付通货膨胀, 重庆政府对公教人员实行发放生活补助费和米代金制度, 以政府公务员及公立学校教职员本人原薪金水平为基数, 并考虑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数量, 发放数倍于其薪金的生活补助费, 同时为保障基本食粮供应, 发放折合一定现金数量的实物米。据档案材料所载, 1944 年时地质调查所职员薪金标准是: 原薪金外加五倍生
活补助费和1500 元的米代金。生活补助费和米代金已远远超过法定薪金。
据1944 年1 月份《地调查所职员生活补助费名册》, 全体员工生活补助费在预算经费的经常费、事业费项下分别支出。其中由经常费项下补助者73 人, 支出99250 元, 人均1359 元; 由事业费项下补助者17 人, 支出21940 元, 人均约1290元。两项合计共为121190 元。
但是, 在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下, 这些补助显得杯水车薪。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震研究的开拓者李善邦, 为了维持家中生活不得不把心爱的宠物猫卖了, 补贴家用。
地质调查所虽也为改善所内职员生活状况做出了种种努力, 然而效果甚微。因为作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 地质调查所为职员谋取福利的措施必然要受制于政府的财务报销制度。例如, 抗战时期成立的西北分所地处气候寒冷的兰州, 冬季取暖费用也成为科学家们一项不小的负担。所长李春昱虽毅然决定以煤炭补助费名义,“无眷者每人一次发付八百元, 有眷者每人一次发付千元, 在事业费内列入煤款报
销”, 但也时时担心着“将来必遭审计之驳下”。
除政府所发固定生活补助费外, 地质调查所也设法争取临时性的生活补助或津贴。1946 年初, 中基会受美国援华会委托办理“特别研究补助金”, 对教授级科学家们予以生活补助。由于名额限制, 地质调查所推荐的候选人有黄汲清、尹赞勋、侯光炯、李善邦、李春昱、熊毅、李连捷等12 人。按每名3 万元标准, 地质调查所共获得36 万元补助。
为了能给更多困难者以补助, 地质调查所按家庭负担、孩子多少的情况, 将该款实际分给了14 人。有的每人3 万, 有的每人2.5 万, 最少的每人2 万元。
总之, 尽管煞费筹措, 但因受种种限制, 地质调查所职员福利改善的“实际效果甚微”。李春昱也时常抱怨:“实有力不从心之苦, 而无奈何也。”科学研究是一种连续不断持之以恒的工作过程, 因而持久稳定且充裕的科研经费, 包括科学家的经济收入, 是维持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民国时期政府对科学事业的投入及科学家经济收入呈现的是每况愈下的趋势, 虽然科学家们仍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推动了科技进步, 但中国科学事业因经济问题所遭受的损害难以估量。
在这个大街小巷随时随处充满着种种周年纪念喧嚣气氛的城市, 在这个以“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的国家首都, 几乎没有人记得90 年前那件发生在北京一条胡同里的事情, 那个对中国历史、社会及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正有价值的日子。这篇短文也算是对90 年来以科学研究为职业, 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辈科学家们的一种敬意和纪念吧。
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4 卷第3 期(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