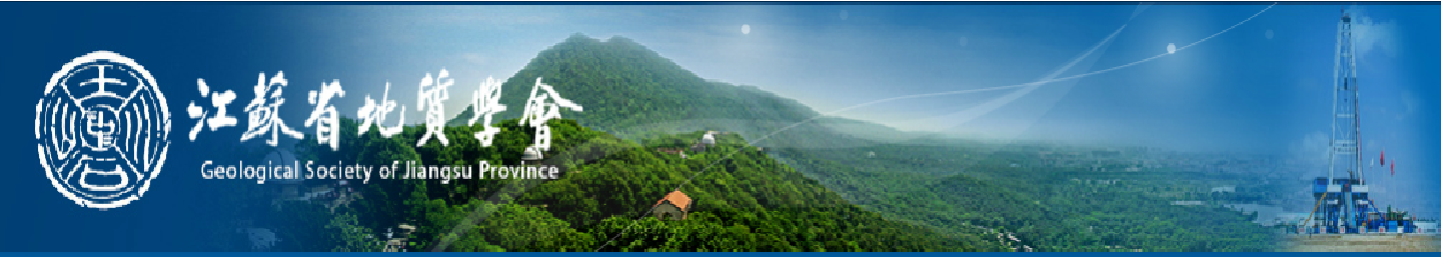
——以巴尔博、李四光对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韩琦 宋元明
摘 要 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是地质学界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这场争论自李四光1921年宣称在华北发现相关遗迹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31年,李四光关于庐山冰川遗迹的重要发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以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最具代表性。作为早期中国地质事业的“客卿”,巴尔博早在1920年代即来华开展了一系列的地质学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1934年,身在美国的巴氏再度受邀来华参加长江流域新生代地质考察,并与李四光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一问题展开论辩,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反映了地质调查所中外地质学家合作的独特模式。作为事件的余波,1949年后李四光对此次论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体现了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地质学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 巴尔博 李四光 第四纪冰川遗迹 新生代 地质学 本土化
作者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 100190)、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太原 030006);宋元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0)。
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是地质学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自上世纪20年代李四光宣布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始,争论就一直未曾停歇,至30年代,李四光和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1890~1977)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展开了讨论,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强烈兴趣。对这场争论的研究散见于地质学论著之中,亦有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
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涉及到新生代气候,乃至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一问题的提出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地质学界引起轰动,与当时学者对人类起源和新生代地质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这次争论的起因如何?巴尔博为何受邀参与?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何关系?本文将根据新发现的巴尔博往来书信、回忆录,结合相关地质学论著,试图探究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国际合作的真实场景,梳理巴氏在华地质学研究,厘清此次论辩的相关史实,分析1949年前后李四光对这场争论的不同表述及其政治背景,以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早期中国地质事业中的“客卿”
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成绩最为突出的当属地质学。早在1912年,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章鸿钊就提出了成立地质调查和地质人员培训机构的构想。次年,丁文江主持建立了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开始培养地质学人才。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地质事业创建伊始,丁文江等人就十分重视与外国学者的合作。他们受雇于地质调查所,为中国服务,被形象地称为“客卿”,在短时间内地质研究能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客卿”的帮助。
民国初期最为重要的“客卿”首推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1914年,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地质学家安特生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的身份来华从事地质调查工作,并于翌年春结识了从云南返京的丁文江。安氏带领学生赴多地实习,为年轻学者提供支持,还与丁文江签署合作协议,商讨化石采集、刊物出版等事宜,寻求瑞典的资金和学者的合作,进行古生物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他帮助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构建了国际学术交往的网络,并邀请赫勒(Thore Gustaf Halle,1884~1964)、师丹斯基(Otto Zdansky,1894~1988)等专家来华,从事古植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作为周口店遗址的发现者,他在1926年特意安排瑞典皇储的中国之行,并在10月22日的欢迎会上宣布了“北京人”牙齿化石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世界。安氏积极奔走,不仅为周口店的发掘事业成功造势,更与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一起争取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
自1919年起,《地质汇报》(1919)、《地质专报》(1920)、《中国古生物志》(1922)和《中国地质学会志》(1922)相继创刊,用英、中、法、德等多国文字出版。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共有创始会员26名,其中外籍人士3名,同年又增加普通会员36名,其中外籍人士多达19人。中国地质调查所还与瑞典、法国、美国的地质和古生物研究机构及博物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国地质学界国际化的情形。所有这些,都与丁文江、安特生等人的努力筹划密不可分。
继安特生之后,来华西方地质学家逐渐增多,其中与中国学者合作最为密切的当属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德日进与地质调查所联系密切,1929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成立,该室的任务是从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和化石研究,还包括对整个中国新生代古生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丁文江任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步达生对该室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他“目光四射,完全以新生代之一般研究为对象,企图解决与原始人类有关之一切问题。故于成立之初,即注意中国新生代地层及古生物之研究,地文、冰川、考古等均包括在内。”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安排下,德日进、杨钟健二人自1929年起两赴山西,足迹还遍及陕西、河北、东三省、两广等地,这些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新生代研究贡献颇多。此外,他们还一同参加了美国中亚考察团第五次考察。在这些考察中,时有巴尔博的身影,他的加入与他在中国的地质研究密切相关。
二、巴尔博对中国地质的研究
从事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学者,大约都会知道巴尔博在黄土和张家口地质方面的工作。巴尔博,苏格兰地质学家,出生于爱丁堡,1911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开始环球旅行,到过中国,见证了辛亥革命。次年,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深造。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1920年,与妻子多萝西(Dorothy D. Barbour)被英国伦敦会派往燕京大学任教。
1921年1月16日,巴尔博抵达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亲往火车站迎接。1920~1921年,华北五省遭遇特大旱灾,巴氏受邀为华洋义赈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勘探地质,在直隶西南调查地下水源,掘井五千余口,缓解了灾情。后发表数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果说对北京地下水的研究是巴尔博在中国的首秀,那么随后对张家口地区地质的系列考察则是他在地质学界立足的基石。
1921年,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为寻找古人类发源地,派遣中亚考察团来华,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1922年9月,考察团首次考察返程途中,在首席地质学家勃吉(Charles P. Berkey,1867~1955)的建议下,由毛里士(Frederick K. Morris)带队对万全县进入蒙古一线的广大区域进行调查。在团长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的盛情邀请下,巴尔博、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和地质调查所的孙云铸加入队伍。此次考察,为巴尔博的学术生涯开启了新的方向。此后他又受翁文灏之邀,对张家口商贸路线两侧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可以说,巴氏在中国的地质学研究,以对华北地文地质发育的研究最为知名,而张家口地区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域。从1922至1926年的四年间,他利用暑期对此区域进行考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1927年5月23日,巴尔博离开北京,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和答辩,司徒雷登亲自驾车送行。1928年,博士论文《张家口地区地质》(The Geology of the Kalgan Area)完稿,文中提出“两个侵蚀期之间被一个堆积期隔开”这一地文期划分方面的重要观点。他通过调查,修正和补充了由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安特生等人提出的华北地文期划分方法,将其分为北台期、唐县期、汾河期、三门期、清水期、马兰期以及板桥期等阶段,初步建立起华北地文循环模式。
巴尔博不仅是华北地文研究的先行者,还较早开展了对中国黄土的研究。他于1925年发表《中国黄土》一文,从化学、矿物、物理及土壤特性等方面对中国黄土进行分析,不仅介绍了欧美黄土以及中国的次生黄土,还对黄土的分布、年代、起源、堆积及垂直节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926年5月,他与新常富(Erik Nyström,1879~1963)、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Percy Dudgeon Quensel(1881~1966)、孙健初等人一同前往晋北考察。1929年,他在《张家口附近地质志》一文中分析了华北黄土的年代及其性质,对黄土与冰期、间冰期等气候因素的关系多有论述,并区分了原生黄土和次生黄土。
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步达生之梦想乃是“将新生代研究室成为一最完备之研究室”,尽量使每一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并训练专门人才。杨钟健负责脊椎动物化石及地层方面的工作,裴文中有志于考古及研究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地文方面一时无人,需请外国人协助,巴尔博于是成为步氏眼中的合适人选。1929年9月13日前后,巴氏重返燕大,随即参与新生代研究室和周口店发掘的相关工作。
就在当年发掘行将结束之际,巴尔博与步达生、翁文灏等人于10月17日前往周口店进行了最后一次视察。12月2日,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引起巨大轰动。巴尔博立即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写报道,宣传这一重大发现。次年,他另一篇关于周口店的文章也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这些报道对于提高“北京人”化石的国际知名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其他古人类学家不同,巴尔博更关注通过地质研究来解决古人类的年代问题。1930年3月、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他两次前往山西太原、太谷等地,试图弄清黄河流域上新世和更新世历史,从而帮助确定“北京人”的年代。1931年6~9月,他在内蒙、陕西、甘肃等地进行考察;10月下旬,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展开合作,在喻德渊的陪同下对南京附近地质进行调查,并于12月初向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提交多份报告,阐述了自己对该地区地质的看法。他还致函李四光,对刘季辰、赵汝钧以及谢家荣的部分观点提出质疑。这几次考察的内容皆与新生代研究密切相关。
随着工作的开展,巴尔博对黄土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他与安特生一样,赞同李希霍芬(Ferdinand Fer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和维理士的黄土风成说观点,反对冲积成因的假说。当然,巴氏更关注与他研究相关的地文期,1934年进一步将堆积期与侵蚀期作了如下的划分:保德期堆积、汾河期侵蚀、泥河湾期堆积、周口店期堆积、清水期侵蚀、马兰期堆积和板桥期侵蚀。
1935年,巴尔博将黄土及其相关地层分为黄土、红色土(三门层)及红土(保德层)三类,认为红色土与黄土均属风成,还与土壤学家梭颇(James Thorp,1896~1984)展开讨论,认定化石土壤皆发源于红色土,并将黄土之化学成分与其他类似土壤进行比较。
三、巴尔博再次来华的背景
1931年12月11日,巴尔博因儿子健康问题举家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1933年,步达生为弄清上新世和更新世地质年代的关联,需要从更大的范围内调查第四纪地质。相较于成果较多的华北地文研究,长江流域之研究则略显匮乏,因此步氏产生了对此区域进行考察的想法,因研究华北地文出名的巴尔博再次进入他的视野。6月,丁文江、葛利普、德日进、步达生等赴华盛顿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巴尔博作为美国地质学会秘书,参与了此次大会的组织。会议期间,步达生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来年赴华考察长江流域的地文,甚至还计划在此后一同穿越西藏,以期达到将北京人化石与欧洲、洛杉矶类似化石联系起来之目的。正是此次考察,巴氏与庐山冰川遗迹的研究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3年11月12日晚8点半,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年会上,李四光发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长演讲,内容为他所发现的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并辅有幻灯片。此次演讲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并引发热烈讨论,葛利普、翁文灏、谢家荣、杨钟健、德日进、新常富及那林(Erik Norin,1895~1982)均参与讨论,其中德日进、葛利普等人对庐山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
11月21日,巴尔博接到步达生以新生代研究室名义发来的正式邀请电报。30日,德日进致信巴尔博,对他接受步达生的计划表示高兴,认为巴氏此次来华非常“值得”,理由有二:一、周口店有了最新发现,德日进希望可以与巴尔博一同对周口店及山西太谷进行调查;二、李四光11月12日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做了关于庐山冰川问题的报告,德日进虽不相信李氏认定的庐山周边广泛分布泥砾,但肯定了这些观察证明秦岭南部及长江中游地区晚上新世的巨大侵蚀十分明显,并认为与李氏合作开展长江中游的调查是必要而紧迫的。
12月6日,步达生亦致信巴尔博,谈到他与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和德日进当天聚会讨论新生代的一些问题,大家一致欢迎巴氏来华。丁文江还希望巴氏来华可以在北大开设地文学系列讲座,以激发人们对地文学特别是新生代地文的兴趣。步达生认为,无论李四光关于庐山冰川问题的判断是否正确,对长江流域进行一次相关调查都很有必要。如果李氏观点正确,那就可能需要重新修正他们此前关于新生代气候的看法。信中提到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准备绘制一份中国北部从甘肃往东的地形图(在蓬蒂阶向上的新生代不同阶段),这一任务加上巴尔博对周口店地区局部地文的详细研究,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步氏坚信,对于他们此前在中国北部遇到的有关新生代特殊问题而言,长江流域藏有破解这些问题的线索。可见,德日进和步达生都对此次长江流域及庐山冰川遗迹的考察极为重视。
接到步氏之信后,巴尔博于1934年1月3日回信告之自己将于3月27日抵达上海,还谈到在华的工作时间问题,并表示愿接受丁文江之邀,在北京大学进行6次演讲;同时他也准备好和李四光开展合作,对翁文灏的友好邀请表示感谢。至此,双方关于考察的具体事宜已基本协商完毕。2月,巴尔博按计划离开美国前往上海。
对于地质调查所来说,1934年初可谓多事之秋。2月16日,所长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发生车祸,卧病杭州,生命一度垂危。3月15日,步达生因心脏病发作在办公室猝然去世。次日,巴尔博在檀香山接到步氏去世的电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对此深感忧虑,认为这会导致中国人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经费用在自己人身上,后续的西藏之旅也极有可能因此取消。
四、长江流域新生代地质考察
此时杨钟健、德日进已从北平启程,前往上海迎候巴尔博。二人在上海得到了汤元吉的招待,参观了震旦博物院(Musée Heude)。2月25日,丁文江自北平南下,驻留沪杭一月有余,期间与杨钟健、德日进同往杭州广济医院探视翁文灏。3月27日,巴氏抵达上海,随后与德日进、杨钟健一同赴宁,由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朱森陪同,在南京附近进行地质旅行。驻宁期间,他们还专程前往句容茅山考察新生代地质及地文发育,在浮山附近察看玄武岩。4月11日,与随后加入的那林一同乘船西上安庆。次日搭船前往九江,与自北平出发经南京赶来的李四光会合,一同搭汽车前往庐山。4月中旬,一行人在庐山停留数天,对庐山各重要地点进行了详细勘察。
庐山之行结束后,李四光、喻德渊返回南京。巴尔博、杨钟健、德日进和那林则前往汉口,受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招待。因急于返回北平,他们随即沿平汉线往北到祁家湾、横店等地观察,并上鸡公山考察地质,下山后即乘火车赴北平。抵平后,他们考察了周口店,参加了5月11日举行的步达生追悼会,与丁文江等人会晤。就在此时,德、巴两人与丁文江在南下目的地问题上产生分歧,因他们并不重视长江下游的冰川现象,希望从汉口往西开辟新区。可能因为地质调查所先前在这些区域有过不少调查,为避免重复,丁文江主张在汉口以东多看看。经过协商,他们商定西行到万县为止。
北平事毕,一行人再次踏上旅途。5月13日,三人南下汉口,杨钟健、巴尔博受邀在武大演讲周口店工作情形。稍事停留后,继续西行,经赤壁、沙市,20日抵达宜昌。在附近的南沱、洋溪等处察看地质后,搭乘美国轮船,经三峡,过巫山、夔州、云阳,抵达万县,决定返程再在此处考察,故继续西行忠州、丰都,最终抵达重庆。他们在重庆与卢作孚、何北衡等人接洽,处理了相关事务。不过在随后的行程计划上,杨钟健与德、巴两人意见相左,认为应按原先计划在重庆附近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再返回万县。但巴尔博、德日进则希望继续西去成都。双方随即分头行动,杨钟健前往北碚,德日进、巴尔博前往成都和灌县。待德、巴两人回返重庆,三人同赴万县,参观了谷兰阶(Walter Granger,1872~1941)所采掘过的盐井沟。后沿江而下,在宜昌进行了地质旅行,踏上归途。6月18日,返回北平。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巴尔博留在北平,撰写此次考察报告。其间受孔祥熙之邀前往山西,遂与德日进飞赴太原,同行诸人获得了阎锡山的热情招待,随后前往太谷,参观了铭贤学校和孔祥熙宅院。
长江流域地质调查结束后,为对比黄河及汉江流域的地文,决定对秦岭东部进行调查。巴尔博、德日进、卞美年(杨钟健因病未能参加,故由卞代)7月17日自北平出发,前往洛阳。他们从洛阳往西南,经长水、卢氏盆地、峪堂沟、黄沙、北峪、西峡口至淅川,又东向过内乡、南阳至许昌,全程穿越东秦岭,获得了不少新材料。8月13日,一行人回到北平。8月20日前后,巴尔博乘火车离开北平,从东北经莫斯科、柏林,最后抵达英国伦敦,结束了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赴庐山考察冰川遗迹是长江流域考察的重要部分,地质调查所试图借助中外合作考察的契机解决这一学术争议,此时距李四光首次提出在中国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已有十余年。
五、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兴起
李四光,著名地质学家,近代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职。长期以来,他都被视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对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四光对冰川问题产生兴趣,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1年,李四光率领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到邢台地区和大同盆地作野外实习,于沙河县沙源岭和大同盆地意外发现边缘圆滑、带有擦痕的巨大漂砾,他相信这些是挽近冰川作用的重要佐证。次年1月,他在英国《地质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第四纪冰川的文章——《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从此便开始了对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追寻和研究。5月26日,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常会上做了题为《中国更新世冰川作用证据》(Evidence of Pleistocene Glaciation in China)的报告,将所见的某些特殊堆积物和地形现象提请与会人员注意,并展示了一些条痕石。此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不过他对李四光列举证据的真实意义表示强烈质疑。后来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安氏指出秦皇岛的一些残积物如果曾被冰流扫荡,则不会保留原处。此外,他还认为条痕石的成因难以解释。李四光也深感问题复杂,暂将此事搁置。
近十年之后,李四光有了新的发现。1931年,他带学生赴庐山实习,其间意外发现疑似冰川遗迹,于是开始重新关注这一问题。1933年夏,他再赴庐山寻求证据。同年11月,李氏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报告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刊出,从庐山冰川遗迹的地貌证据、冰川堆积、冰碛物、各次冰期冰川的分布、冰期时代、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冰川现象等方面详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主要从地貌和堆积两方面来进行论证,地貌上的证据有平底谷、U形谷、悬谷、冰斗和冰窖、雪坡和粒雪盆地。但是相较地貌,他更侧重寻找堆积方面的证据,指出庐山上下皆有大量泥砾堆积,一处泥砾组成的陡崖中多数砾石直径达数尺,风化磨损较浅,混杂于疏松的红色砂质粘土中,砾石含量高于粘土,两者均不成层次。泥砾层还往往形成垄和鼓丘,它们与低地上的泥砾作扇形联展分布于王家坡U谷口与鄱阳湖岸之间的平缓地带。很多巨大的砾石不仅在粘土中存在,有时竟堆积在高出湖面130米的丘陵顶部。
1933年12月初,李四光与步达生就中国更新世气候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李氏认为长江流域的特定地貌以及特殊沉积是冰川活动所导致,步达生做出了谨慎而机敏的回应,尽管有自己的倾向,但仍热情主张对该地区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甚至表示:“如果真理需要,我们必须准备着面对将白天变成黑夜的危机。”
为促成这一问题的尽快解决,1934年4月地质调查所安排了一次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庐山之行。巴尔博、李四光、德日进、杨钟健、那林、喻德渊一行六人在九江会合后,从莲花洞上庐山,在牯岭附近查看悬谷地形,在山上考察五老峰等处,后由含鄱口下山,往白鹿洞,转往青山,至蛙马石,再到马祖山,随后返回九江。李四光以主讲人的身份引导大家观看了他所认为的冰川遗迹,一一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但巴尔博仍持反对观点,认为李氏的很多证据并不可信,很多现象虽然很难用冰川作用之外的理由去解释,但冰川最惯常的特征却未有发现。同行的德日进、那林亦持怀疑态度,杨钟健则以非专业为由没有表态。
六、巴尔博与李四光的庐山冰川之争
从1934年3月27日到达上海,到8月20日前后离开北平,巴尔博这次来华考察历时5个月之久。在结束庐山考察之后,经武汉返回北平的火车上,巴氏完成了有关庐山冰川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他发表两篇文章,正式对李四光的观点作出回应。他认为李氏的说法虽有合理性,但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下结论为时过早,并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首先,判别强烈的冰川作用需要大量的冰川沉积证据,而不是相对次要的冰川擦痕,而庐山并不具备确切无误的冰川地貌特征。一些类似冰川的地形,既可能是流水侵蚀所成,也可能是山体原有的形态。即便风化作用和崩积作用可能会影响冰川作用后留下的痕迹,但冰水沉积、冰砾阜、冰河沙堆、季候泥等重要证据缺乏,李氏的结论难以信服。不仅如此,冰川刻蚀特征以及羊背石的缺乏也同样带来很多问题。而庐山周围大面积的泥砾堆积,也是用冰川成因难以解释的。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他在文末并未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仅表示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讨论。
不久,巴尔博在长江考察的总结报告《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中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李四光所提出的重要论据——“一种不呈层次并大小混杂(最大者口径可达六英尺)之石英岩石块杂出于红色粘土中”——不足以证明存在冰川遗迹,因为还有许多重要的冰川征象尚未找到。对于上述证据,同样可以用别的原因解答:“(一)就土色及石质论,其时代恐不能新于第四纪,或者与我人所见之上梯级层相当(汉中期);(二)即使确系冰川所成,则其发生必甚早,或属于中新统,即大致相当于秦岭期之时代;(三)如上述之砾石层,若谓为系一种深受风化剥蚀,复经山崩土裂,因而聚积而成者亦未尝不可。”再结合此次在长江上游及河南鸡公山等处调查,“虽仔细搜求,未见有何冰川遗迹。昔维理士穿越秦岭自渭河到汉水时,亦曾注意此问题,但冰川遗痕始终未见;由此而论,则李氏之冰川理论,或将不能成立乎?”
此次考察结束不久,巴尔博便离开中国,前往英国。1934年12月,李四光应邀前往英国讲学,两人亦有接触。李氏在伦敦、剑桥、牛津、都伯林、伯明翰等地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The Geology of China),该书提到了他所见的庐山冰川痕迹以及巴氏等人的观点。在此期间,李四光应伯明翰大学地质系教授威尔士(Leonard Johnston Wills,1884~1979)之邀,一道考察英伦三岛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之后,和李春昱、王恒升一起再次赴阿尔卑斯山区考察冰川现象。1936年,巴氏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gtze)一文,在场的李四光进行了点评。
除巴尔博之外,德日进亦多次质疑李四光的论断。1935年,他与杨钟健在《扬子江流域新生代地层之层序》一文中指出庐山泥砾是第三纪末与第四纪的急流沉积物。次年,他又发表《中国之大陆沉积》一文,对李氏的论点提出四方面质疑,认为庐山不存在更新世冰川,泥砾的成因是泥流和洪流,而非冰川作用。
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具说服力,李四光也逐渐将目光投向庐山之外的地区。1934年,他发表《关于研究长江下游冰川问题材料》一文,进一步扩大了冰川研究的地域范围,对安徽中部、九华山、天目山等长江下游区域进行研究。1936年5月5日,李四光讲学返国抵达上海,随即前往安徽黄山进行考察,著有《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上述两篇文章主要根据与此前研究中同样的证据(主要是泥砾),将这些地方作为经受过更新世冰川作用的山地,推断长江谷地曾广泛经历过一次冰川气候。之后他再次前往庐山作进一步的研究。
1937年抗战爆发前,李四光完成《冰期之庐山》(Quaternary Glaciation in the Lushan Area, Central China),综合此前研究,详尽论述庐山冰川问题。文中除描述新发现的季候泥与羊背石外,还专门写了一章“冰碛物释疑”,对非冰川论者提出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与反驳。对于泥砾的成因问题,他认为:一、并非岩石风化所成,因泥砾仅在山北特多,而山南及东北端几乎绝迹,同类岩石在同一气候下之变化不可能相差如此之大,且泥砾中夹杂的大石块只能用冰川作用才能解释其移动的原因;二、不是扇形停积所成,因庐山四周皆有大断层,过断层之后又无斜坡,不利于扇形停积的发生,且泥砾离山远去颗粒变大的现象也与扇形停积特征不符;三、不是山崩作用所成,此与扇形停积的解释类似,根据周围地质条件并不能用山崩作用合理解释其成因。据此,李氏再次肯定泥砾的冰川成因。至于泥碛层上之红泥,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泥砾沉积时是湿热气候,而只能说明沉积和湿热作用并不同时发生,恰好证明了各次冰期后有间冰期的存在。至于庐山南麓没有冰碛物的现象,则是由于山南温度略高所致。最后,关于王家坡U形谷的形成,他认为既不能用构造控制也不能用后期充填解释,而只能用冰川作用解释。此文虽作于1937年,因抗战直到1947年才得以发表,也算是对巴尔博等人质疑的迟到回应。
尽管巴、李二人学术观点迥然不同,但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李四光在1939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一书导言中专门对巴尔博在更新世气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表示感谢,在第九章“中国更新世气候”中对巴氏在黄土和更新世气候方面的研究更是多有引用。巴氏归国后,讨论告一段落,然而这场论辩却在十多年后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波澜。
七、庐山冰川问题的余波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环境剧变。伴随着抗美援朝的进行,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社会上掀起了批判帝国主义的潮流。与此同时,李四光对外国学者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庐山冰川问题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安特生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安特生是最早对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提出质疑的人。1934年,李四光曾回忆1922年与他讨论华北发现条痕石时的场景,提到安特生“有怀疑的理由。我认为他所持的怀疑态度是严肃的”。从中可看出当时李四光对安氏的怀疑持理解的态度。然而,安氏后来却因为此事成为了他口诛笔伐的对象。
1951年12月30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十届年会,李四光以理事长的身份作了长篇报告,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从普通的学术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将之视为外国地质学家破坏地质事业的典型案例进行控诉,报告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地质论评》、《光明日报》等报刊,引起强烈反响。与他1934年描写的场景不同,安特生的形象在此发生了巨大转变,李四光写道:
在我们地质学会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并且采集了带冰擦条痕的漂砾,回到北京。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内幕指导地质调查所工作,他看了我所带回的材料以后,一笑置之。安特生曾经参加过南极探险,而又是来自冰川遗迹很多的一个西北欧的国家。照道理讲,他是应该认识什么样的石头是冰川漂砾,至少他应该认识带什么样擦痕的漂砾,可能是来自冰川的,他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对那些材料很轻视地置之一笑,使我大吃一惊。他那一笑不打紧,可绕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无意地不理会冰川现象的一个圈子。由于这个圈子的把持,第四纪地质问题以及其它有关问题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被李四光点名批判的还有莫利斯(即毛里士)、葛利普、巴尔博、德日进、步达生、费师孟(Hermann von Wissmann,1895-1979)等人。1975年,李氏《中国第四纪冰川》论文集出版,在出版说明中他重提旧事:“尽管证据确凿,但那些外国专家为了维持其既有的看法,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有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并断然否定中国第四纪有过冰川活动。当时,我国一部分地质、地理学家,也就默认了中国第四纪没有冰川存在的看法。”
受李四光批判的不仅有外国学者,连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丁文江也未能幸免。李四光在报告中将他视为“买办学者”,对自己在书中怀念丁氏之举展开自我检讨,甚至控诉:“欺负我最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人(笔者按,即丁文江)。然而他死了以后,我还要瞒着我的良心恭维他:说什么他一生苦心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来表示我的宽宏大度,我这种虚伪的态度,岂不是自欺欺人?”这与丁文江逝世时他所展现出来的态度截然不同。
李四光对这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的批评究竟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还是环境所迫,后人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态度转变与时势环境密不可分,他的这些表态迎合了政治上的需要。
受大环境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李四光,另一位当事人杨钟健在李氏逝世(1971年4月)后的次年8月,即在名为《回忆与忏悔》的文章中对自己在冰川问题中的态度进行了深刻反省,自称当时“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严重地受了德日进等一些外国人的影响,也觉得中国的冰川是可疑的”,并对李四光“真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受外国人的拘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行为表示钦佩。9月20日,他在另一篇题为《论冰川》的文章中再次歌颂了李四光勇于与外国学者斗争的精神;11月2日,在纪念李四光的文章中又一次称赞李氏“不为外国邪说所束缚的精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德日进等特别以冰川专家自居的那琳,抱着成见,不肯面对事实,而顽强的反对李先生的看法”。随后他还做了自我检讨:“我那时既不很了解(说完全不了解,也不见得。因为我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区看了许多冰川遗迹),也没有斗争的勇气,竟采取骑墙态度,不置可否。李先生对我这一点显然是不大满意的,但仍然对我非常客气,使我至今不忘。”
1973年3-4月,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第四纪冰川地质学习班。学习期间,一些地质学家对第四纪冰川地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发言。杨钟健在发言中回忆了当年的庐山之行:
我们的李先生做过的庐山冰川,这里有到过的没有,我到过。庐山的冰川从山顶上算起,从山上一直到鄱阳湖边,虾蟆石就是个冰川的石头,去的时候,洋人也去了,里面有那林,所谓冰川学家。你那林能认识你们斯堪的纳维亚冰川,到庐山就不认识了?莫名其妙,不是不认识。还有巴尔博。这些人有不可告人的成见在里面。科学不能搞成见,科学是科学,你有成见,就不成其为科学了。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去世。而在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杨氏对庐山之行时自己对冰川的看法则一笔带过,仅称自己“适于此时患腹泻,未能尽量发挥工作能力。关于冰川问题,大家意见未能一致。”这段回忆文字与他1934年长江考察游记中的记载基本一致。从杨氏态度的微妙变化中,亦可看到时代的烙印。
至此,庐山冰川之争已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在李四光反帝爱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后数十年间,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呈一面倒的态势,反对者亦多有顾虑,公开发声者更是屈指可数。1960年代虽有辩论,但因环境所限,亦无下文。直到80年代之后,有关争论才重新兴起。
八、余论
民国时期,一批西方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巴尔博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位。他不仅在中国地质学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还发挥专业所长,积极与中国学者探讨学术问题。在华期间,他和中国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博士论文中,不仅对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谭锡畴、王恒升表示了感谢,也对在北大地质系任职的李四光致以敬意。而李四光作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能够勇于面对各方质疑,不断在实地考察中寻找证据进行回应。
1934年的长江考察和庐山之行是一次机缘巧合下的中外合作,庐山冰川遗迹的学术价值不仅限于地文学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新生代气候问题紧密关联。正是在步达生、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巴尔博的此次来华才得以最终成行。随后,巴、李二人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就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问题展开讨论。这场长达数年的辩论,在民国时期中外地质学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颇具代表性,对于促进中国地质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中国地质调查所充分利用资金,由中方组织和主导,聘请欧美“客卿”进行合作考察,既考察和研究了中国地质,也训练和培养了随团的中国学者。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外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中国地质学的国际化,也加速了其本土化进程。1949年以后,受政治环境影响,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一度受到歪曲。随着意识形态对史学影响的逐步淡化,以及相关档案材料的开放,我们最终得以重新认识近代科学史上的这场著名争论。近些年,学界对庐山冰川问题的讨论进入了新的阶段,论辩双方也在陆续提出新的证据,不过至今仍未有定论。无论将来的结论如何,李四光、巴尔博等这批早期地质学家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所做的努力以及对真理的追求都值得尊敬和学习。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编号:KZZD-EW-TZ-01)]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in Ge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Debate on 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 in China between G. B. Barbour and J. S. Lee
Han Qi; Song Yuanming
Abstract: Whether there is 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geological field. The debate started in the 1920s and has lasted for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Based on newly found letters and a diary of G. B. Barbour,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geology in China and introduces Barbour’s work in China. Then it analyses the debate between G. B. Barbour and J. S. Lee in its academic context. Furthermore, it demonstrates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geologist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geology in China.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change of Lee’s attitude toward this debate around 1949 within its political context.
Key word: G. B. Barbour, J. S. Lee, 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 Cenozoic, geology, localization
原文有大量引用标注,如需了解请点击下方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