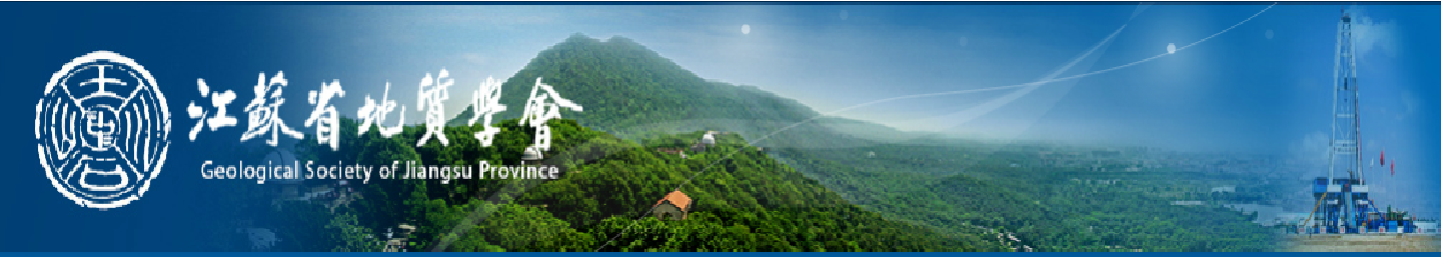对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回忆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地质学是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一门学科。截止到1949年,地质学领域的全国性综合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共有3个:中央地质调查所(1916年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28年成立)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1940年成立);省立的地质调查机构也有十几个。
中央地质调查所(简称地质调查所)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科学研究机构。该所从成立到1950年全国地质机构改组时解体,共存在了近40年。地质调查所的本部早期设在北京,后迁往南京。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又曾迁到长沙、重庆。除本部外,地质调查所曾设立北平分所、西北分所和两个办事处、一个工作站。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尹赞勋和李春昱曾经先后担任该所所长或代理所长,所内职工最多时曾有10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地质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地质学研究机构都是在地质调查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目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仍然健在的学者近60人。他们分布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汉、长沙、西安、天津、沈阳、太原、贵阳、成都、广州、青岛、大连、合肥、台北、美国等地,其中以北京和南京的学者最多。笔者从2000年底即开始着手关于地质调查所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并通过采访与通信的方式,与20多位学者取得了联系,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料。这里仅选择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主题汇编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 被访者简历
胡承志,1917年生,山东,1931年毕业于励志中学,同年入所。
熊尚元,1911年生,四川,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入所,1938年离所。
崔克信,1909年生,河北,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1939年离所。
叶连俊,1914年生,山东,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
陈秉范,1915年生,江苏,193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1946年离所。
徐铁良,1919年生,广东,194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1946年离所。
陈梦熊,1917年生,江苏,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同年入所。
李星学,1917年生,湖南,1942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
乔作栻,194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
程伯容,1920年生,江苏,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农学院,同年入所。
何金海,1918年生,河北,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同年入所。
于天仁,1920年生,山东,1945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同年入所。
沈永和,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
盛金章,1921年生,江苏,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同年入所。
朱显谟,1915年生,上海,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壤农化系,1947年入所。
姜国杰,1916年生,福建,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1950年入所。
鲁如坤,1926年生,河南,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年入所。
王遵亲,1925年生,山东,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年入所。
桂乃钰,1924年生,南京,1947年入所。
夏晓和,1925年生,湖北,1947年入所。
彭 会,1919年生,香港,1943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附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转业,后在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当处长,
负责地质机构的接管工作。
二,被访者谈中央地质调查所
★ 进入地质学领域的原因
黄汲清(转引[1]):我选择地质专业,兴趣当然有一点,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其实我的初衷是想在外教门下把英语学得更好――当时我已有一定的英语基础,还翻译过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而北大的理科中,就地质系有外教。于是我就填报了地质系。 尹赞勋(转引[2]):我原本想学习化学,后又开始向往哲学。因哲学系名额已满,改入中国文学系读书,一年以后又转入哲学系。我在同学的劝说下,决定赴德留学,学习经济学,而中途又改变主意,留在法国学习地质学。 杨钟健(转引[3]):为什么入地质系?我自己当时也莫名其妙,大约只是因为没有别的系可入。那时候(北大)理学院只有四系:数学、物理、化学和地质。我因数学根基甚差,所以根本不感兴趣;又因不愿闻实验室气味,所以也不想学化学;地质系有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很有意思,所以入了地质系。还有,我两年前不能入文科,为的是家中人总要我学些实用科学,地质虽不是实用科学,而究竟和矿冶等科接近些。我又不愿学医,只有学这与矿冶接近的地质了。 阮维周(转引[4]):(在北大)读预科时,我原想读化学系,但两年的预科后,认识地质系是理学院最好的一系,所以决定进地质系。 叶连俊:我原来没有选择地质学,准备考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结果我们那一批就录取了一个,我没有考上。第二年我去考上海交大。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及格了才能参加复试。初试考西洋史,要用英文答卷。考试时中午管一顿午餐,吃沙拉等西餐,我吃完后就拉痢疾。而且那时考试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考试的头天晚上我去看戏了,结果也没考好。后来我又去考燕京大学,到那一看,燕京大学的考卷有一、二尺长,就在考卷上划正负号,划错了还扣分。我一看就不干了,准备收拾行李回济南。同来的人劝我考北大,好一起走。我考取了,进入北大后在选系的时候我想上物理系,但成绩不够。他们让我去数学系,但我看到数学系里有好几个大教授,却只有一、二个学生,我不愿意去。我的一个老乡在北大读书,他说北大地质系很有名,有丁文江、李四光,还有一个外国人。我问学这个有什么用,他说:你将来可以开矿,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我想暂时先在这呆着,将来再考别的。我进了地质系之后,我们家人就劝我在这念,说是再考很麻烦。
李星学: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5]。我搞地质,既有必然因素,又有偶然因素。 我有一个舅舅叫朱森。我八岁左右住在外婆家里,朱森在北大念书时暑假期间经常回家。他对学习抓得很紧,回家后还到家乡附近的山上去采化石标本。那时我跟着他去采标本。我记得他采了一块很大的化石,无法带到北京。后来他就打了块小一点的化石,并带到北京,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报》上[6]。他走时就把那块大的化石标本放在床底下。家里人觉得没什么用,就把它扔在外面。我因为曾跟着他采标本,觉得石头很好看,就又把石头搬了回来。这样小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朦胧的印象。 我初中的时候在武汉博文中学冬季班念书,高中博文中学只有夏季班。我就考到湖南长沙雅礼中学。学校有一个科学馆,有二、三层楼。第二层楼是教室,在第一、二层楼之间的墙上,贴着当时世界上著名科学家的画像,有哥白尼、牛顿、居里夫人……,都是外国人像。1936年1月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忽然看见那里挂了一个中国人的像,戴金丝眼镜、留八字胡子。我很奇怪,就问物理老师。他讲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家,是地质学家丁文江,非常了不起。老师还告诉我们:“丁文江昨天在湘雅医院去世了”。
30年代末我考取了金陵大学、同济大学。那时我报的是物理学和医学。选择物理学是因为过去教我们的物理老师很好,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选择医学是由于我父亲是医生。但抗战的时候这两个大学都搬到四川去了。我后来到了重庆,我的舅舅朱森在重庆大学地质系当教授,我去看他,他劝我跟他学地质。因为我有考取大学的证明,于是就在重庆大学借读。
崔克信:我考入北大预科两年以后开始选系,原本想读物理学。但想到我的家乡有煤矿,学了地质将来毕业后可以到煤矿当工程师,所以就选择了地质系。而且那时地质系有几个世界有名的教授,像葛利普、丁文江、李四光等。我的几个同乡也都说地质系好,我就入了地质系。
陈梦熊:我哥哥在清华大学,他知道北大地质系很有名。我在中学的时候没有地质学课程,但我对地理学课程很感兴趣。后来我哥哥跟我讲地质学跟开发矿业有关系,我觉得地质学和地理学又有联系,就考虑选择地质专业。1937年我到了北京,准备考大学。当时我考的是北方交大、燕京大学,考的是物理系,这几所大学都没有地质系。我连金陵大学也考了,而且都考取了。但很快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大、清华没能在北京招生,我无法入学了。我就从北京逃难到南京,从南京到广州、香港,又到上海,上海那时成了沦陷区内的孤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西南联大招考。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里面有地学系[7]。我想,考地学系到不错,于是就报考并考取了。那时地学系大概也就录取了三个人。后来我查了一下,真正到昆明去的就我一个人。 陈秉范:地理学包罗万象,训练通才。地质学则重专才,寻觅财源,……对大政治家与实业巨子有很大帮助,但就业范围很小。至于我选择地质学,一方面是受历史人物江阴徐霞客的影响;另一方面因当时地学领袖的贡献而发生兴趣。再者是由于我对山水的爱好。我想了解山水,不是地理学的山水,而是地质学的山水。
沈永和:我个人选择地质学并非是由于我对地质学的理解与认识,只是感觉地质学可能更适合我。如果说对地质学有点兴趣,那也是以后慢慢培养起来的。
姜国杰:我年轻时想学哲学,但是研究哲学需要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所以就选择了地质学。地质学调查研究的对象是随地而异,每有创新,这类工作比较容易出成果,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所以有志之士愿意为之献身,各方面也乐于捐助与支持。
盛金章:我毕业于重庆国立二中。当时上的是春季班,寒假毕业。毕业时大学还没有招生,离考大学还有一段时间。于是我就到一个乡中心小学当教员。当时没在城里,一个原因是日本飞机常常去轰炸,城里不安全。另一个原因是想利用教小学的机会多看一些书,准备暑假考大学。去了以后不到一个月,学校里就告诉我说可以保送我上大学,让我填表。那时我也年轻、贪玩,填完表我就不再复习功课了。结果时间临近考试,可是保送的事情却一直没有消息,我很着急,于是只好和其他同学一起结伴去参加考试。由于没有准备,我在考数学时好多都不会,只做了两道题,结果考卷都没交我就回去了。那时大学不是统一考试,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很多学生都同时报考几个学校。学习好的学生就会同时被几个大学录取。因此一些学校招收的学生没去报道,招不满学生学校就会再次招生。
我回去后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第二次招生时,重庆大学有几个没有招满的系又要招生,其中有地质系。因为我在小学教历史、地理等课程,那时也不知道地质学是研究什么的,觉得它与地理接近,于是就报了地质系,并考上了。到重庆大学报到后一个月,我就收到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单。四川大学在成都,那时从重庆到成都很不容易,要走好几天,而且还需要一笔路费,我们家是逃难去四川的,经济很困难。我就没去四川大学报道,从此进入地质学领域。
★ 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的原因
杨钟健(转引[8]):大学中“教授因限于设备与环境,能做研究工作者甚少,与其慕虚名而无所得,反不如在地质调查所安心作些实际工作”。 崔克信:当时地质调查所选取高校地质系学习好的学生到那里工作。我在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同学中阮维周、李悦言成绩排在前两名,因为他们家庭经济条件好,毕业时被安排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我的学习也不错,但因家庭经济困难,系里的老师考虑安排我留校当助教。当时助教月薪80元,到地质调查所月薪只有50元。有一天系主任孙云铸见到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系里决定留你当助教。但我想地质学是野外科学,不跑野外无法提高。所以我说我不想当助教,想到地质调查所工作。我做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房山的地质问题[9],我的论文得了奖。我就把论文拿给所长翁文灏看,但他没时间看。毕业后我考入了地质调查所。 叶连俊:我们毕业时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响了。我们一毕业,系里的教师谢家荣就安排我们考地质调查所。有十几个人参考,地质调查所只录取了六个。
盛金章:地质调查所聚集的一批著名地质学家,像黄汲清、尹赞勋、杨钟健……不但是国内著名学者,在国际上也都是很知名的学者。而且所里有一个很好的地质图书馆,藏书很多,要想做学问的话,这个地方确实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946年我毕业时找工作很困难。地质调查所是通过考试选人,这为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班当时有9个毕业生,大多数都去参加考试了,个别的同学找到了工作,比如去当中学教师、做生意等。后来有4个学生被录取了。
李星学:国内地质学界的地质精英大概有三分之二都在地质调查所,所以我们对这个地方很慕名。翁文灏有个外甥叫李庆远,他是学地貌的,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资源委员会当专员。我毕业时他希望我当他的助手,那是个好位置,坐办公室,待遇也好,大概一个月有120元。初进地质调查所工资才60元。我不想当官,想搞地质研究,所以没有去资源委员会。当时我们系有五六个人考地质调查所,就考上我一个人。
熊尚元:1933年我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就由化学系的高宗熙老师介绍给北平地质调查所沁源燃料研究室的主任金开英。沁源燃料研究室的学者都不是搞地质的,全部是学化学的。金开英跟我是前后同学。那时金开英自己反对一个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工作。但他刚从美国回来,对国内人员情况不熟,大概只有找高宗熙要人,高宗熙推荐了杨珠瀚,1932年燃料研究室又要了一个人,是宾果,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到第三年高宗熙介绍我去工作。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来自清华。
陈梦熊:我大学毕业时,孙云铸是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在他的鼓励下,我考入了地质调查所。
胡承志:因为在这里不但可以做本职工作,还能学到很多东西。要是在大学教书,不但野外考察机会少,而且因为没有经费,也只能在本省的小范围内考察。地质调查所的学者都是权威性的,所以大家都愿意入所工作。虽然在所中工作比较清贫,但在这里对提高业务是有好处的。
★地质调查所的工作环境
沈永和:地质调查所发展很快,我认为一是初期领导人员很强;二是注意培养人才,早期大多数人员都送出去学习,并照顾到各分支学科;三是重视调查研究和成果的出版;四是从业人员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和敬业精神;五是注重国内外地质文献资料的搜集与保存。
熊尚元:地质调查所经费很少,都是丁文江、翁文灏出去募捐得来的。燃料研究室的经费也是地质调查所支付,所以也是紧得很。我记得燃料研究室要花五块钱买一个器皿,还得找翁文灏批。而且地质调查所的工资比较低。
李星学:地质调查所没有派系的争斗,在这一点上确实很难得。地质调查所是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一个小机构,靠国民党政府机构拨钱。它在政府机关里,在党派争斗的环境中并没有官气,没有党团的扰乱,是个清水衙门,很难能可贵。所以地质调查所除了学风好以外,它学术发展与没有党派在其中搅乱也是很重要的。
地质调查所好就好在当时的领导人都非常正直,都是博学的学者。他们的学风、德风都非常好。像丁文江、翁文灏都曾做过官,但他们都视地质调查所为学术圣地,不愿意把坏的东西带到地质调查所。所以在地质调查所形成了好的传统。像黄汲清、尹赞勋等都当过所长,但一旦从所长的位置上下来,他照样干研究工作,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当官去。新的所长上任,也不带什么亲朋好友。
陈梦熊:地质调查所是一个开放型的研究所,当时常有外部门的专家来所,进行短期的研究工作。这也是一个优点,它可以自由和外面交流。那时侯一方面表现在人员调动比较多,另一方面表现在各个研究室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特别是室主任是很少变的。像区域地质包括大地构造室主任一直是黄汲清先生。岩石、岩矿、矿床室一直都是程裕淇先生,古生物室始终就是尹赞勋先生,他们当所长时也同时还兼室主任。解放以后就是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基础上建成了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了。东北和广东土壤所的骨干人员也都是由南京土壤研究所分出去的。同样调查所地球物理研究室的成员,像李善邦、秦馨菱等成为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骨干力量。当时每一个室人并不多,像古脊椎、古人类研究室不超过20个人,可工作成绩突出,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姜国杰:地质调查所各研究室先后设置,比较齐全。所里的学者也很正派。地质调查所在体制上有其独到之处,不但有广泛的经济来源,而且研究环境也很不错,办公、野外考察条件在当时都很好。……堪称中国地学的发祥地。我所在的工程地质研究室成立最晚,当时只有四个人,现在全国搞此类工程地质工作与研究的何止四百人、四千人。但我毕业时没有直接去地质调查所,而是去交通部帮助搞地质调查。我在大学时为了收集资料,曾去过地质调查所,感觉那里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很厉害。解放初期我才到地质调查所,在那里和军管会的同事配合得很好。
程伯容:当时地质调查所研究经费十分短缺,时常由调查煤矿所获得的回报分给全所各研究室作为野外调查研究之用。人员也少,几乎所有行政事务性工作都由科技人员兼管。我觉得科学研究单位人员不宜过于庞大,行政事务工作要尽量由科研人员兼管。
刚进所人员都先进行培训,以便适应工作需要。……虽然经费少,我们每年仍然能够进行实地土壤调查工作。我们时常自己带着行军床,住在老乡家里或寺庙里。
叶连俊:在所中大家相处得很好。我们刚入所时,所中的老大哥都对我们很好。夏天时我们没钱,他们就买个瓜放在所里,让我们吃。
盛金章:我们的宿舍也在所里面,晚上基本上都在办公室里。因为我们那时工资非常低,像我一个月拿80元,我们同学中在南京市政府工作的一个月能拿到150元。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地质调查所学术气氛好、环境也很好。宿舍就在所里,晚上到办公室看看书,很清静、很幽雅。人事关系也好处。没有像一些官僚机关还需要送礼,也没有像其它机关还有国民、三青团等的政治影响。地质调查所好像没有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当时所里哪些人是国民党党员,只知道当时绘图室的颜慧敏好像在管着这些事。具体他们做什么平时也看不出来,他们也不会来管我们。
我们有时打桥牌,有时也比赛篮球,当时西楼和东楼搞比赛,很热闹。记得经常是马溶之主持。当然参加者主要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像我们室主任尹赞勋,他就是两点一线,一个家一个办公室。
胡承志:凡是进了地质调查所的行政干部,不是搞地质的、也不是搞技术的,来到地质调查所都感到奇怪,晚上办公室都亮着灯。业余时间大家仍然用于学习或工作,娱乐活动很少。也就是每一年春节前开一个同乐会,演个话剧,唱一段京剧等。每周一的纪念周地质调查所都要搞学术活动。所长先讲一些所务性的事情,然后就是学术报告。在地质调查所学术风气特别浓,很难看到哪个人整天在那晃、聊天。
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事情好像在地质调查所很少发生。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你搞你的矿物,我搞我的岩石。在学术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用我的话讲,地质学研究就是自由主义加浪漫主义。因为这个学科涉猎范围太大。
★ 野外地质调查工作的回忆
盛金章:搞地质研究的学者都希望能够经常到野外考察,因为研究工作需要接触实际,必须要跑野外。但跑野外需要经费,没有经费就去不了。
陈梦熊:那时野外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仍然愿意到野外去调查。因为这是对专业的一种爱好吧。要么你就不搞地质工作,要搞地质工作就要到野外。跑野外虽然有危险,不过当时很少有人考虑遇到土匪等问题。比如1942年的贵州地质调查,我和陈康、许德佑、王钰四个人分成两组,陈康和许德佑是一组,我跟王钰是一组。我们是到黔东北考察,就是遵义、湄潭一带,那条路线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首先去拜访土匪头子,送礼。然后他给你一个名片,这个名片就等于通行证,可以通行无阻。我们在考察时遇到好几次土匪,不是抢我们,是把人家打死在公路上。好在我们有通行证。第二年我就到兰州西北分所去了。1943年马以思入所工作,她是所里第一位女地质学家。第二年许德佑、马以思和陈康三个人继续在黔西南工作,那一带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国民党时代的社会治安很差,他们就在那里遇难了。后来查明杀害许德佑等人的土匪头子就是那个县的参议会议长的儿子。参议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协。所以土匪也就是官,官也就是匪。当时地质调查所很重视这件事,因为死了三个人,而且死得也很惨。所以翁文灏直接打电报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要他必须把凶手抓出来。要不是省主席亲自来干预这件事,凶手根本就抓不了。
那时地质人员之间竞争也很激烈,专业人员每人都要求进步。搞这个专业就要写论文。评工资、升级,主要就根据你的贡献,看你写的考察报告。那时除提交考察报告以外,都要写一些研究论文。看你发表论文的多少、好坏。那时刊物也不多,最重要的就是《地质论评》[10]、《中国地质学会志》[11],你一发表文章,大家马上就看到了。所以地质调查所的传统就是学术空气特别浓厚。每个星期都有学术研讨会,每个人从野外回来都要做报告。或者请外面的专家教授做报告。所以不管是在南京也好、在重庆也好,晚上所有办公室的灯光都亮着。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另外从所长到室主任,到下面的研究人员都在搞研究工作。 叶连俊:当时搞野外调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30年代末,秦岭一带的老百姓连30年以后的税都交了,所以到了下半年没饭吃。我们野外考察到过一些小地方,一般是到县公署去找地方住。一次我和关士聪在野外考察时住在安康的一个县城里。我们在外面吃饭,吃完饭后交钱,伙计说:你们不用给钱。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们来,我们还得交钱呢。我一听就火了,他们竞以我们的名义剥削老百姓。我们出门时碰上了县公署的人刚好磨面回来,我们就上前问他:我们吃饭自己交钱,你们为什么要老百姓的钱。三说两说就打起来了,我们把他拿的面也给扣在地下了。这件事惹了祸。我们下一站到了另一个县城,那个县城很小,从一个城门就可以跟另外一个城门上的人说话。我们刚刚住下,县长就带一帮人来了。县长指着我们带的捆行李用的绳子说:城门前挂国旗的绳子丢了,是不是你们干的?并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关了十几天,我们身上的虱子有小米粒那么大。后来我们偷偷给所长发了一封信,所长尹赞勋给甘肃省建设厅长写了封信,这才把我们放了。放我们的时候县长还说:出了我这个县界你们的安全我们概不负责。到了省里以后我们就到省政府去告他们,告了也没用。
40年代我和李承三去调查地质,到了宜宾时正赶上日本人在轰炸。我那时得了恶性疟疾,住在一个教会医院里,结果来了几个洋鬼子,赶我走。我那时身体很虚弱,扶着墙走出了医院。有几个挑滑杆的人挺好,抬着我出了城,找到一个旅店让我住在那里。店里一听说我的病,不让我住。给我喝了两碗水,让挑夫抬着我上山。我带着治病的药,按规定一天只能吃一粒,吃多了就有生命危险。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把一瓶都给吃了。天无绝人之路,出去跑了一天我到感觉好点了,但回来以后店里还是不让我住。挑夫又把我抬回城里,我在城门碰见李承三。他是个很重感情人,见到我就哭了。头一天晚上日本人轰炸,李承三跑到一个洞里面躲了一夜,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胳膊抬不起来了,得了半身不遂。他把我接到河对岸,买了一只鸡,炖鸡汤给我吃。我吃不下去,他就让我喝汤,他把鸡肉吃了。我养了大概一个月身体才逐渐恢复。于是我们接着往前走,正好走到土匪打死赵亚曾[12]的地方。我们两人就住在赵亚曾当年被打死的那间房子里面,当时的枪眼还在。 崔克信:那时野外考察很危险。1941年丁道衡[13]带着他的一个学生做助手,两个人到西康考察。结果遇到土匪。丁道衡个子很魁梧,穿着一个粗呢子的衣服,看上去像个有钱人,让土匪盯上了。结果在去巴唐的路上被抢了,他的学生胳膊上中了一枪,他们被抢得身上只剩下短裤和背心了,那时天气很冷,他们只好裹着马鞍下面的垫子,走到一个县城。 我那时考察的区域多在藏族聚居区,所以很注意跟藏族的翻译搞好关系。一次在野外吃午饭的时候,看到过来一个人,身上带着长枪、短枪,骑着一批马,手里还牵着一批马,一看就是土匪。他说是去做生意,我们知道他不是好人,但还是请他坐下来一块吃饭。就听他和翻译说话。我也懂一点藏文,听土匪问:“这个人官大不大?”翻译说:“很大”。“有多大?”“县长请吃饭,司令员不但招待,还亲自送了十几里路”。这些都是实际情况,因为我们是省政府派去的,县长、司令都很热情,而且我们也很谈得来。但是翻译如果对你不好,他就不会帮你说话。而且翻译告诉土匪:“我们没带什么东西,都是各县招待我们”。土匪一了解官大、又没带值钱东西,就没抢我们。我们经常会和土匪在一起吃饭,虽然有危险,但都应付过去了。
李星学:20世纪40年代我们曾到宁夏去调查。由重庆先坐资源委员会往西北运油的大卡车到甘肃平梁,然后步行北上。首先是地质调查所与资源委员会打交道,他们让我们免费乘车。到宁夏后该省就派一个科长和一个科员接待我们。后来那个科员一直陪着我们工作。去的时候是六月初,离开宁夏的时候是十二月三十一号。宁夏那时在马鸿逵统治下实行血腥统治,哪个地方出了事情,就要地方清查交待,有时一杀就是十几个。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倒没什么危险。我们离开地质调查所时,侯德封再三交待我们要注意安全,因为他三十年代去过宁夏,他说你们四、五点钟以后千万不要出城,否则就没命。我们去时那里的治安情况很好。
学地质的人非走穷山荒野不可。我们在宁夏葫芦斯台考察,现在是一个大煤矿。当时没有开发,那里有很多化石。我与边兆祥两个人一起考察,我们分工合作,一个人打化石,一个人做地质路线。头一天是他打化石我做路线,走到一个岔路口,我向他打招呼告诉他前进的方向,以为他看见我了。他从沟里打化石出来,走到岔路口看见有人远远地往另一个方向走了,他就去追,结果一晚上都没追上,后来凌晨两、三点钟在一个蒙古包里过的夜。第三天我量地层,他做路线。我好不容易爬上一个二、三百米的高山,等到山顶上已经天近傍晚。下山时并没有我想像得那么容易,山路拐到别了地方了。那时天已经黑了。贺兰山里面根本就没有几户人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也就两、三户人家。我知道离住处也就十来里路,但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地方猪背形砂岩构造很多,走来走去地形都差不多。结果一直走到8、9点钟也找不到路,我很害怕。没办法,又爬回山头。我们有个经验,大声叫时,附近有人家就有狗叫。但是因为那里人少,怎么喊也没回声。又怕叫声把狼招来。最后爬上爬下,在一个山顶看到前头7、8百米远处有火光,有火光就有人家。我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罗盘,对准那个地方,走了半个钟头。走到那里却只看到有一堆火,没有人,旁边还有一个骆驼。我也不管了,就坐在火旁边。十几分钟后,一个人跑了出来。他竟然怕我!一是怕我是坏人;二是因为他是在走私大米,怕被抓到。我告诉他不要害怕,我不是坏人。他知道我的住处,我给了他五元钱,他把我带回住处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我有一次一个人在浙西考察,特地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脸盆挂在挑行李的担上。这样我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这样万一出事别人好找,坏人不敢轻易动手。
[1] 尹传红,黄汲清:万千苦涩不了情,《科技日报》,1994年8月26日,第2版。 [2] 尹赞勋,《往事漫忆》,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6-10页。 [3]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4] 杨翠华,《阮维周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2页。 [5] 参见《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72页。 [6] 朱森,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地质学会会志》,1928,7(1):61-80。 [7] 该系全称为“地质地理气象系”,又简称为“地学系”。 [8] 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136-168页。 [9] 崔克信,“河北省房山县周口店附近地质”,1936年获北平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奖金”100元。地质矿产研究奖金自1930年开始每年办理一次,1936年共收到申请论文10份,经奖金审查委员会评议,共有4人得奖。(《地质论评》,1936,1(2):221)。 [10] 《地质论评》,创刊于1936年2月,以“刊登文字以关于地质学之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为限”。 [11] 《中国地质学会志》,创刊于1922年。主要刊载会员调查研究报告和学会年会宣读的论文等。专业性较强,用英、德、法等文字写成,并附有中文目录。对于两刊的区别,翁文灏指出:“……《会志》……以期宣达于世界;……《论评》……以期介绍于国人”(翁文灏,《中国地质学会概况·序》,转引自夏湘蓉等,《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12] 赵亚曾(1898-1929),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入地质调查所工作。1929年在云南昭通地质考察途中被土匪杀害,年仅31岁。 [13] 丁道衡(1899-1955),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1930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30年代留学德国,学习古生物学。1939年回国,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1940-1942年任武汉大学(嘉定)教授;1942年开始任贵州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并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