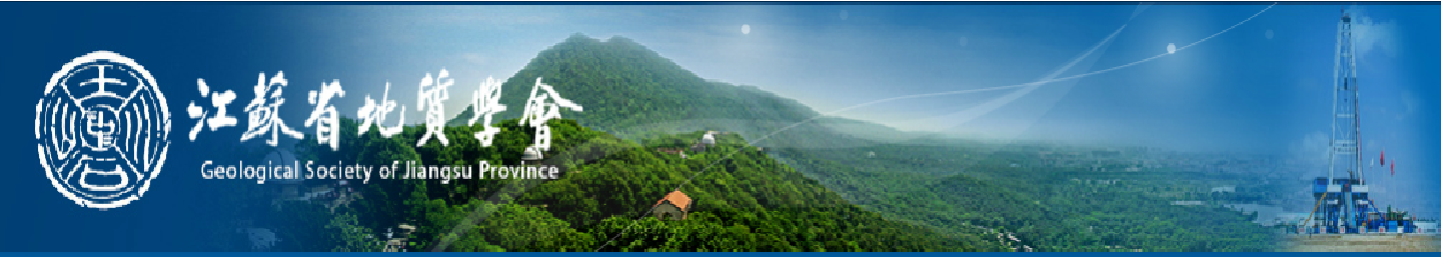
抗战时期许德佑等三地质专家遇难案述评
李学通
内容摘要:1944年春,中央地质调查所三位在野外从事地质考察的科学家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贵州晴隆惨遭土匪杀害。案发后,为使凶手伏法、遗属遗孤获得抚恤,翁文灏及地质学界地人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社会资源。土壤学家侯学煜施巧计骗得土匪口供,终使案件告破,凶手伏法。最终,遗属遗孤获得抚恤,许德佑等获国民政府颁令褒扬,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黯然辞职。惨案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科学所面临的艰难境遇,以及科学家们忍辱负重的悲惨经历。
关键词:抗日战争 许德佑 陈康 马以思 地质调查所
1944年春,在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贵州省,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三位正在野外从事地质考察的科学家在晴隆县惨遭杀害。一时间朝野震动,中国科学家在战时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国家、为科学埋头苦干,而生命安全却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悲惨经历,引起人们的关注。对这起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空前的惨案,近年虽仍有缅怀纪念性文字发表,而各种相关记述中对具体史事或已语焉不详或已矛盾丛出。今检索相关历史文献档案,略加梳理考证,以存史实,并试图从中分析近代中国科学事业所面临的困境。
许德佑陈康马以思被害经过
这起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空前的惨案,1944年4月24日发生在贵州省晴隆县的黄厂,被害者是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许德佑、技佐陈康和女练习员马以思。
许德佑,江苏丹阳人,生于1908年,毕业于上海澄衷中学,1927年入复旦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兼修社会科学,1928年转入政治学系。大学时代的许德佑堪称文艺青年,曾参加田汉、洪深创办的南国艺术院,创办《摩登》杂志,热心于文学戏剧活动。1930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入蒙伯里大学地质系学习。留学期间,他仍然不断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介绍欧洲电影、戏剧以及国际政治的文章,如《今日的法兰西戏剧运动》(《小说月报》第22卷第12号)、《拉丁民族的电影艺术》(《时事新报电影周刊》)、《法意亲善声中之两国外交政策检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7号)等。1935年春毕业,获硕士学位,随后在巴黎大学古生物研究室,从事白垩纪甲壳类及石炭纪珊瑚化石研究。1935年夏回国,11月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技士。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地质调查所西迁长沙,后迁重庆北碚。1942年升任技正兼任该所古生物研究室无脊椎组主任。地质调查所对他的评价是“勇于任事,和蔼近人”。自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至其牺牲时止,十年间前后共21次赴野外工作,发表中外文古生物学论文29篇,“尤以研究三叠纪地层及化石为国内仅有之专家,国外同道均知其名”。1940年获中国地质学会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44年获中央研究院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学金。
陈康,广东番禺人,生于1916年8月,中学就读于广州勷勤中学,1937年考入陈济棠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字勷勤)成立的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后改称广东文理学院),就读博物系。因为他特别喜欢地学,在校时即对广东连县地质进行深入研究,著成《连县东坡连山大掌岭之沿途地质概况》一文。1941年夏毕业后,先入两广地质调查所,与莫柱蒸、刘连捷合著《乐昌九峰地质矿产》。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坡之地质》由校方送教育部审查核时,评阅人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地质学家黄汲清。他们对陈康的论文“深为赞赏”,于是推荐其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陈康1942年9月进入地质调查所后,先任练习员,1943年9月升任委任五级技佐。他曾随许德佑调查贵州安顺、平坝一带地质,并整理该所自南京带到重庆的化石标本。所里对他的评价是“工作努力,兼长绘画”,他随许德佑所采集的化石,多由他自行描绘。
马以思,女,回族,原籍四川成都,出生于黑龙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家庭先后迁济南、上海,抗战爆发后入川。1939年毕业于国立二中,入大学先修班,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毕业后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任练习员。马以思人极聪慧,“历次大中小学曾考第一名者28次”,曾获林森奖学金及上海银行奖学金。她不仅通英、德文,而且兼习法、俄、日文。毕业论文《黔北桐梓县之下三叠纪动物群》,首次对贵州黔北桐梓地区介形类的化石进行了研究和定名。进入地质调查所后,跟随许德佑从事古生物研究,整理该所化石标本,“井然有条,甚著伟绩”。她是地质调查所招收的第一位女性地质学者。此次随许德佑赴贵州调查,也是她入所后的第一次野外工作,谁料竟遭此惨祸。
当时许德佑与陈康、马以思刚刚参加完4月1-8日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0届年会,依照所里的计划安排,顺便前往黔西地区测绘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并进行古生物地质调查与标本采集工作。许德佑等三人4月17日抵达盘县,工作三日后,于20日由盘县县城出发,沿旧驿路前进,当晚到达该县杨松场住宿。次日三人又走了60里,抵达普安县兴中乡(罐子窑)。22日在罐子窑附近工作了一天,23日晨由罐子窑继续前行25里,正午到达五里坪,当天在保长叶永昌家住宿一夜。24日,计划由五里坪向茅口前进60里。当许德佑三人行至晴隆县黄厂附近时,被土匪劫杀,不幸遇难。
关于许德佑三人遇难的事实真相,现今著述大都已语焉不详,有些记述则加入了演义的成份,乃至以讹传讹。现依据档案及历史文献记录,梳理如下: 许德佑等三人22日在罐子窑赶场时,无意间被一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此人名叫易仲三,居住在距罐子窑三里的梅花菁。他发现这几位外乡人“行装颇多,购物多用新钞”,于是见财起意,“乃与五里坪惯匪陇占洪计议行劫”。
当时贵州省境内占山为王的大股土匪已不多见,但散则为民,聚则为匪,平时务农,遇有行客即集合抢劫的小股散匪“则到处皆是”。见财起意的易仲三,就是这样一名被土匪们称为“老板”的土匪头子。因为他曾在地方军阀的队伍里混过,当地人称“易营长”,而且还是本地大绅、晴隆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易荣黔的堂侄。在易仲三的指使下,惯匪陇占洪“约集普安及晴隆(安南)两县匪徒20余人”,“分别担任眼线、看哨、挑夫、抢劫等工作,并分数路等候”,准备抢劫。因为这些小股散匪自己并无枪械,易仲三又“连夜派其部下送给各匪步枪三支、连枪二支”。
许德佑等人虽然并不知道他们已被土匪盯上,但是对当地治安情况还是有所警惕。因为地质调查所前辈科学家中,1929年就曾发生过古生物研究室主任赵亚曾在云南野外调查时被土匪抢劫杀害的惨案。在兴中乡停留之时,许德佑就曾向乡长颜绍黔询问区内治安情形。23日行前,又特意请求乡长派壮丁跟随保护。但乡长表示其辖区安全绝对无事,他可以完全负责,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由陇占洪率领的土匪原本在23日已分别在黄厂和花贡两条路上设了埋伏,等候动手,不料许德佑三人因为一路进行地质调查,当晚即在五里坪借宿于保长叶永昌家,因此土匪未能遂其所谋。24日一早,许德佑一行由五里坪出发,继续前行。出发时,保长叶永昌还特意代他们雇了三个挑行李兼做向导的挑夫在前面引路。中午11时左右,他们在假扮挑夫的土匪引导下,来到了距五里坪15里的晴隆县黄厂附近一处僻静地方——土匪预先设好的伏击圈。早已埋伏路旁树林中的9名匪徒一拥而出,走在前面紧跟在挑夫身后约2米地方的许德佑,突然被土匪开枪击中,子弹由腰穿腹而出,当场牺牲。走在后面的陈康、马以思,闻听枪声“即拟奔避”,被匪徒堵住逃路,“鸣枪威吓,无法逃脱,遂至束手被擒”。匪徒们又押着陈康、马以思又向前走了20多里,于下午六时左右将陈康枪杀,抛尸在晴隆县马路河的森林中。虽然马以思义正辞严地警告土匪:“我是大学毕业生、国家官吏,你们都有姐妹,请杀我,勿辱我。”十余名狂悍的匪徒置若罔闻,竟丧尽天良地将马以思轮奸后杀害。匪徒们将三人随身携带的行李财物抢劫一空,共劫得现金53000元及行李、衣服、仪器等。
当许德佑被杀之后,其中一名叫安猎狗的挑夫当即逃离现场,分别向晴隆、普安两个县地方的保甲长报了案。许德佑被害之地距晴隆大田乡乡公所不过20余里,如果当时地方保甲立即组织人员追击,或许陈、马二人仍可获救,然而直到第二天,地方政府方派员出面进行调查。而易仲三竟然大摇大摆地于25日亲自前往五里坪,将五枝枪收回,并分得18000元赃款。
追缉凶手与善后抚恤
在许德佑等三人于普安、晴隆一带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的同时,另一位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从事植物与土壤关系研究的侯学煜,也正在附近的盘县从事科学考察。
侯学煜,安徽和县人,生于1912年,1937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土壤专业,同年入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先后任练习员、调查员。27日上午,已经到达贞丰的侯学煜闻听许德佑被人被害的凶讯后,立即赶回盘县县城,与普安、晴隆两县政府电话核实消息,商议缉凶营救事宜。侯学煜随后打电话向贵州省政府报告,“而省政府当局竟不知此事”。28日,他“又去吴主席一急电,正式报告”。在当天给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的报告中,侯学煜写道:“职心中难过,不可言状,痛哭之余,只有尽量办理善后事宜,或可解遗憾于万一。”“职决定由此带好木匠、漆匠同到出事地点,亲自看守入殓,并自督导油漆”,“一面详细探听被劫情形,再为报告”。
当时正处于抗战期间,事发地又处于交通不便的黔西南,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同仁虽心急如焚,但鞭长莫及。侠肝义胆的侯学煜,虽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人生地不熟,但他毅然赶赴出事地点,担负起追查凶手、办理善后的责任。案发地黄厂虽然属晴隆县辖区,实际上距普安县城100里,距晴隆县城约200里,因此侯学煜先于28日赶到普安县城,“29日晨由普安县城出发,当日下午五时到达出事地点”。
为查明真相,侯学煜坚持首先将三名挑夫拘捕到案,并“亲自参加审讯”。“最初一般匪犯不敢供出主要匪首姓名”,于是侯学煜假称:奉中枢严令,查办此案,如不吐实,立即枪决。挑夫仍不肯说,侯即略施小计,命军士将一挑夫拖出,鸣枪两响,又如法炮制,“枪毙”了另一挑夫,最后挑夫方才供出事实真相:案件背后的主谋人原来就是“众匪称其为老板,当地人又称其为易营长”的“普安兴中乡梅花菁之易仲三”。而且易仲三“在罐子窑时知许君为公务员,意全杀之,使不得破案”。更让侯学煜震惊的是,抢劫杀人在这些土匪看来如家常便饭,“得知这些匪徒杀死了若干若干的过路人,他们把被杀的尸处抛到洞子里或是河边,家属都无法找到。今春有一个卖甘蔗的,只有二百元,他们都把他杀掉。每个匪徒都可以供出若干杀人的案子来。”此次参与抢劫枪杀许德佑三人的土匪共有29人。
虽然当时科学家们在出外调查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都呈文上级主管部门经济部,咨请当地政府予以安全保护,但据侯学煜报告“省府方面不过将其转下而已,并无吴主席特别关照之意”。尤其令侯学煜气愤的是,虽然几个小土匪已经抓获,但幕后黑手易仲三却藏匿乡间,逍遥法外。因此他建议所长李春昱:“只有请翁部长转吴主席,严饬该县拿获。”“为防患于未然计,最好请翁部长特请吴主席加以严办。倘如此次再与省府客气,恐以后同样事体发生也”。
事实上,在接到侯学煜最初的报告之后,所长李春昱第一时间立即向该所上级主管长官也是地质调查所前任所长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做了汇报:
“顷接本所土壤室侯学煜君自贵州盘县来电称,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晴隆(安南)廿四遇匪毙命,详情探报等,不胜惊愕。消息确否,尚等证实。当即复电侯君及吴主席,请为查询。候有确讯,再行奉陈。”
翁文灏接到报告后,立即亲自草拟电文,通报贵州省主席吴鼎昌:
“限即刻到。贵阳吴主席达诠兄:密。据中央地质调查所侯学煜自盘县电报,传闻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员在晴隆遇匪毙命。侯君已赶往复查,请兄迅电晴隆县,查明具报,万一不幸遇匪被戕,亦请兄令由晴隆或普安县政府帮助侯君处理后事。至深纫盼。”
为了加强办理善后事宜的力量,避免侯学煜一人在贵州孤军作战,李春昱特加派该所贵州籍的土壤学家熊毅赶赴贵州协助工作。翁文灏又专函时任贵州省财政厅长、代理省主席的周诒春,请求“厚予协助”:
“寄梅先生大鉴:此间接中央地质调查所侯学煜自盘县来电,闻同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人在晴隆普安间遇匪被戕,已赶往查云云。四月三十日弟接讯后,即急电于吴主席达诠兄,请其迅行电县,查明是否属实,万一不幸被戕,即令县政府帮助侯君妥为处理后事。兹者中央地质调查所嘱熊毅(原籍贵州省)专程至筑面洽,然后转往出事地方。专函奉介。敬祈兄念学者牺牲从公之忱,厚予协助,至为企节。”
与此同时,翁文灏又电令在贵阳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地质调查所技正谢家荣予以协助;并命令设于贵阳的资源委员会运输处,对熊毅等办理善后事宜在经费上给予“10万元以内借垫支用”的帮助。
据吴鼎昌5月5日电复翁文灏:
“本案已据本省三区徐专员卯感电及晴隆县府有电称,回日下午中央地质调查所三人中景[普]安县属白沙地方遇匪九人,许君被害,二人被匪架去等情。除已分饬景[普]安、晴隆两县府迅予营救,并对死者妥为处理后事外,特复。”
次日,翁文灏电告吴鼎昌:
“中央地质调查所职员许君被害,陈、马二员被架,承示已分饬景[普]安、晴隆二县府,迅予营救,并对死者处理后事至感。该所现派熊毅专程赴筑,洽办各事必需款项,弟自必设法筹助。对陈、马二人盼迅为救释为感。”
如前文所述,虽然几个小土匪已被抓获,但幕后黑手易仲三却逍遥法外,相关地方单位对缉凶工作并不得力,因此翁文灏5月9日再次致电吴鼎昌,指责地方官员对吴鼎昌的报告“并不尽实”,要求“省府另派专员就地确查”:
“顷阅中央地质调查所侯学煜自普安函报该所李所长函,内言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员已在晴隆县属黄厂附近遇匪,三员均已被害,尸身具在云云。该员等为公务陨命,极深悼惜。为促起地方官员责任起见,不能不请贵省府对晴隆、普安有关治安人员认明实情,认真惩处。读兄上次发电,可见地方报告并不尽实,不免有推委或减轻之意。如不整饬,深恐治安更不易保。最好由省府另派专员,就地确查,庶与实况,且示重视之意。”
为增加对贵州省当局的压力,翁文灏5月13日又电令谢家荣面见吴鼎昌,当面督促省方“迅即拘捕惩办”易仲三。电云:
“据侯学煜函报,许、陈、马三员被劫致死一案,系由易仲三主使、筹枪、分脏。此人为普安易参议长之侄,恐地方官或有瞻顾,请兄即面陈吴主席,迅即拘捕惩办。”
同日,翁也与李春昱联名致电侯学煜,表扬他“办理各事甚为妥切”,要他与谢家荣一同面见吴鼎昌:
“许、陈、马三员遇匪被害后,兄在黔接洽办理各事甚为妥切。所有事实情形恐吴主席或未尽悉,请兄偕季骅兄面向陈明,并请将罪犯迅速拘办。”
5月19日翁文灏再次致电贵州省政府:
“咨请查照迅即严缉凶犯尽法惩处母使有一漏网。据称普安县参议会易议长之侄易仲三为该案主犯,保长叶永昌、乡长颜绍黔均有重大嫌疑,自应逮捕,严加鞫询。至普安、晴隆两县有关治安人员,并应分别查明实情,酌为惩儆,以明责任而饬将来。”
因为道路阻隔,通讯不便,重庆方面直到21日接到侯学煜13日的来函,方才得知易仲三已于5月12日在逃亡中因拒捕被击毙。据侯学煜13日致李春昱的报告称:
“现足以告慰许君等于九泉之下者,即此次枪杀许等之主谋人易仲三已于昨日下午格毙,迄现在止,共已获得匪犯十八名,尚有九名在逃。易匪为此地大绅之后嗣,势力甚大,今春曾杀害补充团某军官,抢其枪械,花了十万元了事。职且知县府当局总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以为县内之匪能少说一个就少负一点责任,对于此案总不愿意扩大匪犯数目。职因知其心理,决心不使一匪漏网,几夜没有就寝,一面设计如何捕拿,一面向外宣布职已呈报中央,匪将此匪拿到不可,使县府方面不能推诿。现职留普之主要目的已达,今明赴晴,再参加审讯该县所获之匪犯。”
就在接到侯学煜来函之后,地质调查所由李善邦领衔,黄汲清、尹赞勋、程裕祺、周宗浚、曾世英、颜惠敏、丁毅、王钰等几位资深学者,还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学员”的名义,直接上书“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本人,报告惨案经过,请其饬令严缉凶犯,惩处地方负责人员,“以彰法治而慰忠魂”。“现已捕获十余人,另有数匪在逃。顷悉主谋易仲三因拒捕格毙,是否确凿,尚待证实。倘该匪漏网,不惟无以正法纪慰死者,亦且贻祸将来。”对当地“或知匪不报,或通匪有嫌,危害忠良”的乡保长,以及“事前姑息养奸,事后动作迟缓”的地方政府给予“应得之罪。”同时要求对“忠勇从公,为国殉职”,“家境清苦,身后萧条”的许德佑等人“特予矜恤”。
有文章称,许德佑等人被害之后,蒋介石曾下令“贵州省兴仁专署和普安、晴隆县政府3天之内侦破此案”等等,也仅是传言而已,并未见档案文献证实。实际上,对于李善邦等人的呈文,“蒋团长”并没有直接回复,而是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转给经济部长翁文灏:“奉谕:交经济部□查,酌情办理。”
许德佑等“家境清苦,身后萧条,或则孤寡无依,横断生计,抚育无资,或则衰父弱母,痛失养老送终之嗣”。尤其是许德佑“所遗寡妻孤子,托避异乡,至堪悲悯。孤碚生,年甫四龄,来日就学成人,在在需款接济”。家属的瞻养、遗孤的教育之资都是非常现实且十分艰巨的难题。因此,在督促贵州地方当局积极缉凶的同时,翁文灏及李春昱等也在积极推动抚恤与褒扬事宜。
无论是按照“组织程序”乃至私人交谊,李春昱当然还是给即是上级主管领导又是地质学界领袖的“咏公夫子”翁文灏打报告。在档案中,有一件未注明日期的翁文灏亲笔批条:“一、行文贵州省府,缉匪严惩;二、呈院,特予抚恤并明令褒扬。速办。文灏。”从内容看,应该是案发不久后翁文灏给经济部下属的批示。
按照当时的组织关系和公文程序,先由地质调查所于5月18日备文上呈经济部,报告案件经过,并提出对许德佑等三人明令褒扬、分别给予特种抚恤金的申请。次日,再由经济部呈文行政院:“除咨请贵州省政府严缉凶犯尽法惩处外,理合具检呈各该员事略,具文呈请,仰祈鉴核,准于例行抚恤外,特拨专款从优给恤”,“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以慰忠魂而励将来”。否则“非特无以慰死者,抑且此后地质调查工作人人视为畏途,恐无法进行,国家损失,不堪设想”。5月21日,李春昱又致函翁文灏,具体商讨遗属的抚恤事宜。他提出:“现在第二步工作,在如何为许君等筹募眷属瞻养及子女教育费”。他认为,“如数目太少,实无济于事”,因此地质调查所同人拟发起向社会募捐活动。他还就募捐由谁出面发起事宜提出三种方案与翁商讨:方案一由翁文灏出名发起;方案二由翁与朱家骅、李四光、吴鼎昌及地质界同人共同发起;方案三由地质调查所或李春昱、尹赞勋发起。但他又以“惟后者恐收获微”,实际否定了第三方案。
最后由朱家骅、翁文灏、李四光、孙云铸、谢家荣、叶良辅、李学清、周赞衡、杨钟健、俞建章、侯德封、张更、乐森寻、王恒升、黄汲清、尹赞勋、李春昱等地质学界著名学者共同发起,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遗属瞻养费及许氏遗孤教育金”举行募捐活动。为了永久纪念三位以身殉职的学者,部分募捐所得由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许德佑先生纪念奖金、陈康先生纪念奖金和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上述三项奖金从1945年开始评审,授予相关学者,其中陈康奖金主要授予青年学者,马以思女士奖金主要以奖励女地质学者为主。
6月11日,中国地质学会与中央地质调查所联合在北碚举行了纪念许德佑陈康马以思遇难追悼会,与会者达200余人。何应钦、白崇禧、朱家骅、李书华、李四光、吴鼎昌、陈果夫、陈立夫、张伯苓、李约瑟等均敬送了挽联诔词,任鸿隽、钱崇澎、俞建章、范旭东等出席。所长李春昱主持并宣读祭文,尹赞勋介绍三人生平经历,特别称赞许德佑“对于全国三叠纪地层之研究甚有贡献”。
6月16日,翁文灏再次致函吴鼎昌,除要求贵州继续认真缉凶,否则“如不认真缉治惩处,不特无以慰已死之三员,亦恐更滋未来之巨患”外,对善后事宜提出五点具体要求:
“一、三员殓后存晴隆,一俟贵阳附近墓工准备告成,运筑安葬。运柩及安葬时,均由省政府令行妥为保护照料。
二、安葬日上午,由经济部及省政府会同在贵阳科学馆开会追悼,下午在墓地安葬时,并各派员参加。
三、省政府允发赙恤三员款十万元,吴主席允捐二万元,均交中央地质调查所组设委员会,连同其他捐恤各款,妥为支配,以慰遗族。
四、县长刘超伦、耿修业出事时适因公离县,但当其在县时,许陈马三员至境,曾经知照,乃保护无方,出此巨变,自应有其责任。其他职员及有关之乡长、保长,办事情形亦不一律。普安县保警大队长徐文蔚,督率所部缉揖匪犯,颇为尽力,盼省政府对于此类人员查明实情,酌予处分或奖励。
五、此次事变,串同作恶之匪徒竟达三十人左右,行为备极惨毒,且据招认夥同开枪杀人劫财已不只一次,动摇治安,杀伤人命,实非寻常劫案可比。除缉捕时格毙五人及已捕获处决者十六人外,据报在逃匪犯至少尚有九人(姓名另列),由省政府严令迅速续缉务获,并将先后缉获匪徒及处分办法函报经济部备查。”
吴鼎昌在18日的回复信中,对上述五项要求全盘接受。他表示:
“地质调查所许、陈、马三君遇害,实堪痛惜,善后诸端,自应照所示五项办法处理。捕获匪犯已于本月四日在普安县处决,在逃匪犯一俟缉获,仍同样置之于法,决无宽贷。昨接贵阳电话,三君灵柩已起运来筑,惟尚未全至,俟安葬有期,即照所示第一二项办理,请释注。”
在各方努力推动之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科学家的灵柩得以运至贵阳,6月21日安葬于花溪,立碑纪念。至6月底,杀害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的土匪先后“就逮及伏法者已达24名”。
8月5日行政院通知经济部,“经提出本院第670次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特恤许德佑五千元,陈康、马以思各三千元”。不久,国民政府也批准了行政院的请示,正式颁布了对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人的褒扬令。
国民政府令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
行政院呈:据经济部呈称,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许德佑、技佐陈康、练习员马以思三员,派往黔西调查地质矿产,惨遭匪徒戕害,转请明令褒扬等情。查许德佑等学有专长,任事勇迈,因公殒命,悯悼同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旌恤。此令。
主 席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蒋中正
战时科学的境遇与挣扎
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工作者竟于野外从事科学工作时遇匪被戕,一时激起人们对战时大后方社会治安状况的质疑和指责,对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环境的不满,以及对科学工作者人生境遇和工作条件的同情。
许德佑、陈康、马以思服务的机构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该所1913年初创于北京,最初名叫工商部矿政司地质调查所。虽然因为主管机构名称的不断更迭,该所先后改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4年时名为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而且所址也于1935年由北平迁至南京,抗战时期又先后迁长沙、重庆,但是其实体一直沿续未断,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尹赞勋先后担任所长或代所长,1944年时所长为李春昱。该所被称蔡元培称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在中国矿产资源,以及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及古人类学、地震学、土壤学、地图学、考古学等许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取得到周口店“北京人”发掘与研究等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成果。“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人的伟大骄傲。”
抗战爆发后,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两次公开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一方面提醒:大家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万不应托名科学而弃了国家”。另一方面要求大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战服务,将急需开发的矿产“从速详确调查,编成图说”。地质调查所跟随国民政府内迁后,科学家们不仅坚持不辍地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和野外考察,而且也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大后方地质矿产资源调查,以直接为后方工矿业发展、为抗战建国贡献力量。以许德佑为例,他不仅继续致力于古生物研究,鉴定化石,撰写发表科学论文,发表学术演讲,还担任着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和会志编辑的工作,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国地质学会年会,编校《中国地质学会志》,代国立编译馆编著中学用博物教科书(普通地质及地史部分),还积极培养青年学者。陈康入所后即跟随他从事古生物学研究,二人共同署名发表了《贵州西南部三叠纪》(《地质论评》第9卷第1-2期合刊,1943年)《 Revision of the Chingyen Triassic Fauna》(《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3卷1943年)等论文。虽然专业领域为三叠纪古生物,但是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从事于矿产资源的调查,并撰写发表了《湖北秭归县香溪煤田地质简报》(《中央地质调查所简报》第19号)和《云南之铝矿》《云南之磷矿》(《资源委员会季刊》第1卷第2期)等矿产资源报告。
就是这样一位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努力贡献于国家社会的科学家,却在从事科学工作中被土匪们无情杀害了。更可悲的是,在地质调查所的历史上,于野外考察中遇匪被害他们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早在1929年,正是许德佑等人所在的古生物研究室,时任研究室主任,中国最年轻最有成就的古生物学者赵亚曾也是在野外地质考察时,于云南昭通遇匪被害。赵亚曾牺牲后,地质调查所与中国地质学会也曾为其遗属抚恤和遗孤抚养教育向社会募捐,并用部分募捐所得设立了“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而1940年度赵亚曾研究补助金的获得者正是许德佑。
许德佑等三人的被害,不可避免地引起地质调查所同人乃至大后方科学界的极大震动和激愤,“全国学术界闻讯,深为震悼”。科学家们的工作环境及生活条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据许德佑的同事、地质调查所前所长黄汲清回忆:抗战爆发,地质调查所内迁重庆北碚后,许德佑因为体质较弱,“所以自奉不敢太薄,在物价飞涨以前,差不多非天天吃肉不可,后来肉渐渐的吃不起了”。可是“要是一礼拜不见肉食,他免不了就要卧床不起!然而肉又这样难得,于是他不得不买书,两三年来竟把历年存书买得干干净净!”“女工也不能雇,他们夫妇只得自己操作。我天天看见他毫无所苦的在堰塘边淘米,还不断的在菜市上遇见他买菜。”
正如黄汲清所说,“同事们年来生活日苦,平日见面免不了大发牢骚,我个人也不能例外。”李春昱也在致翁文灏的信中大泄不满:
“此间所中同仁自德佑等三人死后均受莫大之打击,佥以为生前不获温饱,死后眷属无以为生……生可以大胆说一句话:现在公务人员之所恃以为生者,不外三条途径:一是贪污,二是做生意,三是兼差。而本所无一于此,此所以不堪命他。即以生个人而论,每月除本人伙食零用外,仅余二千余元及米八斗用以养吾之家。除煤水油盐外,每日不能买蔬菜二斤,遑论肉食。其他同人收入较少于生,更无论矣。瞻念前途,恐惶万状。”
对于战时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这种“思想动向”,出身于地质学界的翁文灏当然非常清楚并深为同情,但另一方面身为党国要员的他,也很担心这种情绪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引发非理性的过份举动,破坏稳定大局:会不会有人借死者为名节外生枝,搞什么不利于党国的过分举动?会不会因为对贵州地方当局过多指责过份要求而影响地质调查所乃至经济部与贵州省特别是吴鼎昌的关系?如果许德佑作为国际知名学者而被土匪杀害之事广为传播,会不会因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他的担心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就有人在“赞扬纯粹科学家之赴难精神”的同时,主张“与黑暗斗争,学术机关应以余力为社会尽力,先行改造环境”。李春昱内心虽然也很是愤懑,但作为学生和下属,对于翁文灏的良苦用心还是心领神会:
“钧座所示决不能借死者为名而有过分举动。现所拟捐募者,一切均为丧葬及眷属瞻养、教育之用。对吴主席本所亦从无失敬之举。的确吴主席为目前之贤明疆吏,吾人请求各点,吴主席均允照办。吾人亦无过份之要求,惟为纪念学人起见,曾以下葬花溪与吴主席面商,并告以如实在有不便处,当不相强。吴当告以如自己购地安葬,彼并不反对。故曾函嘱熊毅购买墓地。但如吴主席不肯使葬花溪,未始不可再与家属商量。”
“本所希望吴主席厚遇死者及其眷属则诚有之,而无理之请求则决不发生。”
“至向国外宣布,同人等爱护国家名誉,更无此意。故对外发表经过,亦未曾招待新闻记者。对土匪野蛮行动一概删去,即马女士被污事,亦未告知其家属。”
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为免物伤其类计,善后问题自以尽力为之,方足以慰死者以及自慰。” 并且积极为遗属抚恤遗孤教育问题想方设法。
而且在6月11日的追悼会上,翁文灏以“激奋声调”,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演说:
“本人今天有两点特别感到痛心,第一点地质界人士有百之十四都为工作而死于非命,前仆后继,但是并没有得到社会上人的充分注意。此实在不足以策励将来。第二点,在地方上有人被土匪打死,大家的同情心并无甚多表现,这样重要的学者死去,大家反认为常事,在我们自己固仍常自勉,但地方当局亦应引起自愧。”
他甚至比喻中国科学尚处于黑暗的16世纪:“今日亦如十六世纪,科学家须以不断的牺牲,始得突破黑暗”。翁文灏的演说既说出了知识分子们的心声,代他们发泄了心中的愤慨与不满,但又理性地管控了情绪,做到了“哀而不伤”,最后更勉励同人共同负起责任, “好好作事,好好作人”,一定程度上平复了科学家们“物伤其类”的悲悯与愤怒 。
另一方面,翁文灏也在其职权范围内给许德佑等人的遗属尽可能多地争取了经济的补偿。如前文所述,惨案发生之初,翁文灏即指令资源委员会运输处对熊毅等在贵州办理善后事宜给予10万元以内的经费协助。5月9日,翁文灏有亲笔指令经济部有关部门:“中央地质调查所职员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员在黔西调查遇匪被害,除抚恤办法另行议定外,先即由部垫付十万元交所。”后经李春昱8月8日呈部,以“该款如数领到,惟该员等一行三人同时殉队员,临时收殓、运柩及一切丧葬费用需款已不在少数,且该员等清廉自守,身后萧条,寄寓无石斗之储,遗属绝生养之资,学人厄运,悲悯同深”,请求“体念困厄,准予将已垫付之拾万元悉数作为特别救恤金,以资支应而维遗属。”最后由经济部以“特恤费”名义一笔勾销。而且经由经济部先后呈请行政院批准,财政部国库署1944年12月22日通知地质调查所:“查中央地质调查所故员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等特恤金经改定共为11万元,已由部签发普直字8694、8695、8696、12966号支付书,饬库照拨并通知该所洽领。”一下子将原定许德佑5000元,陈康、马以思各3000元的特恤金,增加到了10倍,从而达到了“慰死者以及自慰”的效果。 虽然在翁文灏、李春昱的多方工作之下,地质学家们并没有提出“无理之请求”,吴鼎昌还是于1944年底辞去了贵州省主席的职务,转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毫无疑问,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遇匪被戕惨案,对自1937年至1944年主黔7年,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以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相标榜的吴鼎昌而言,既是无法回避的尴尬,也绝对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即使知识分子们没有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但是其他方面的压力也不一定没有。据李春昱致翁文灏信中提及,“与本所及川所均无关系,所要求各条,生事前均未闻悉,亦未曾见面”的马以思的姐丈“杨敬之君”,当时正在中央训练团高级训练班受训,想必也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中高级干部。更有一位“允捐拾万元”的“马主席”,乃“马以思亲戚,姑丈抑表姑丈关系”。当时姓马而称主席者,一是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一是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无论是哪一位,他们在国民党政权中的份量和可能施加的影响,当然是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难望项背,甚至是经济部长翁文灏也无法比拟的。
吴鼎昌走了,离开了穷乡僻壤的贵州,而中国科学和科学家们依然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依然在崎岖的路上挣扎。